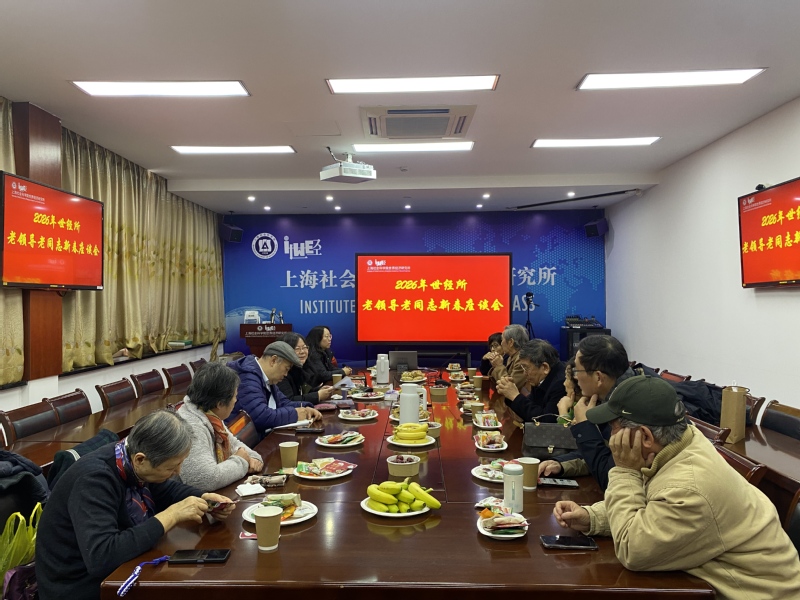曹金玲 韩圣海 郭茹 杨斯媛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新起点。
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下称《意见》),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国家战略层面确立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终于一锤定音。
向前追溯,国家层面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相关部署在18年前就已拉开帷幕。
早在1991年,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曾语重心长地说:“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新飞跃”;2004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2007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意见》出台之际,中国对内面临经济模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发展要求,对外则恰逢全球“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
站在国家战略视角的历史新起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已然超越了一个城市的未来,它同时也肩负着为中国经济探索新增长方式、提高我国的国际金融竞争力以及更好服务全国的重任。
在此背景之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更加令人瞩目:国家战略框架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迎来怎样的历史性机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未来的挑战在哪里?上海通往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又将怎样抉择?
1 国家战略定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2007年10月,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个月后,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屠光绍调任上海市副市长,主管金融。
2007年底起,上海有关方面开始着手进行14个主课题调研,涉及范围非常广,其中光是金融领域就涵盖了土地规划、人才引进、公司税收、地方配套立法等金融环境建设,以及金融创新突破口、创新清单等。这一系列的课题调研基本在2008年上半年结题,调研的相关内容也成了日后《意见》和上海地方性立法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知情人士透露,2008年7月温家宝总理到上海考察后,上海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相关内容中又加上了航运中心和现代制造业的内容,在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进程中,形成了以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的“双子星座”。
2009年3月25日,期待已久的《意见》终于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确定了上海“两业、两中心”的发展战略。4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次“移师”上海召开发布会,这也是国新办首次离开北京举行会议,再度凸显了中央层面对于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重视。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银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表示:“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实际上是站在国家战略的层面上,帮助上海经济完成产业转型,让上海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如何发展中国金融体系、提升中国在世界范围的金融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等联系在一起,也和国内经济转型、新一轮改革开放密不可分,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是上海的事,也是整个国家的事。”
就在中央层面的《意见》下达之际,上海本地的配套政策也在积极制定和完善中,国家部门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推进齐头并进。
今年3月24日,《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草案)》(下称《条例》(草案))正式进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程序,标志着上海第一次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推出金融发展和金融中心建设的地方法规。《条例》(草案)共分8章,内容主要侧重于金融环境和服务质量的考量。
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表示,《条例》(草案)一旦获通过,上海将更好地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尤其在配合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和国家金融中心建设大战略上形成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
“这次《意见》把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一起提出来,实际上也可以说上海接受了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发展应该和实体经济的发展齐头并进,如果不是金融危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步子或许不会像现在这样加快。”上海财经大学MBA学院院长戴国强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表示。
2 上海的机遇和挑战
今年2月,屠光绍在“第一届中国财富与资产管理论坛”上指出,鉴于就业和社会保障带来的压力,确保经济增长是上海的一个首要任务。
“如何形成下一步确保经济增长持续的支撑,这个问题对上海而言显得尤其沉重。”屠光绍当时坦言。他表示,确定下来的有“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其中现代服务业中最关键的是金融业。
事实上,从2003、2004年开始上海的经济增长后劲乏力就已经开始显现,原有的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已初露端倪。要确保上海的经济增长,必须加快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推进“双中心”建设也使得处于经济发展转型关键时期的上海迎来一个优化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的契机。
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目前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在保增长、调结构的过程中,金融的改革、创新和开放必不可少,上海要借自身的优势把金融市场做深做大。上海的发展将离不开中国经济总量的大幅度提升,随着经济总量的提升,上海金融市场本身的规模也将大幅增长。
当然,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道路上,上海有很多功课要做。包括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以及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首要的工作则是先把金融市场做大做强,这样才能在开放后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波谲云诡。
胡汝银指出,一方面国内的金融市场基础仍相对薄弱,已有平台产品仍然匮乏;另一方面金融法制环境也需要改善,“国内金融机构在结构上不完整和金融产品的短缺,又会造成专业人才的缺乏,只要市场发展了,金融人才的培养和吸引都可以很快完成。”
“未来金融中心能否真正建成的关键,是政府控制与市场发展如何保持平衡且形成张力,实现金融市场运作机制的转型,即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最主要的机制。”胡汝银说。
戴国强则强调,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此外部门之间的整体协调也有待加强。
3 协调机制与突破口
西谚云:条条大路通罗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是要在2020年成为“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罗马也不是一天就能够建成的。与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的金融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市场规模还不够大,国际影响力仍然有限。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目标能否如期完成,关键还取决于相关政策措施的具体推行和落实。
此次出台的《意见》初步描绘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远景,《意见》列举了计划在上海实施的关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业务等方面“先行先试”的政策,政策的涵盖兼具广度和深度。如大力发展企业(公司)债券、资产支持债券,开展项目收益债券试点,研究发展外币债券等其他债券品种;研究探索并在条件成熟后推出以股指、汇率、利率、股票、债券、银行贷款等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有序推出新的能源和金属类大宗产品期货等。
继《意见》公布后,上海市政府又于2009年5月11日发布了《意见》的具体实施意见,上海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框架和路径正日渐清晰。
上海金融办主任方星海日前透露,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明确主要任务、责任部门和时间进度的今年“工作表”中,总共统计出80余项具体措施,涵盖了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产品创新和业务体系、稳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共六个领域。
具体内容包括拓展金融市场广度;促进债券市场加快发展;发展上海再保险市场;推进金融综合经营试点;推进地方国有控股金融企业改革和重组,鼓励发展各类股权投资企业(基金);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积极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板建设;适时启动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支持设在上海的合资证券公司、合资基金公司率先扩大开放范围等;根据国际贸易结算试点进展情况,充分发挥上海金融市场在人民币支付清算和市场交易方面的作用,研究在上海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
在不少专家眼中,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试点将成为上海推进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突破口。
“一个国家的货币城市化往往会伴随一个金融中心的诞生。”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近日在上海指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步伐,既能降低中国经济的未来风险,也会给许多金融机构带来好处,可以实行人民币结算,发行人民币债券,吸收更多境外人士的人民币存款等。”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人民币的国际化密切相关。”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周宇说,“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在于人民币业务,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为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由国内转向国际提供契机。”
戴国强也指出,除了人民币结算,国际金融中心最终还是需要实现多币种结算。此外,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市场应该完善和完整。要在金融机构集聚速度加快的基础上,推出适当的金融产品,才能反过来吸引更多人才和机构。
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的机遇与不足
| 2009-03-30 |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代松阳 |
上海的金融市场监管相对严格,但缺乏灵活性;场外交易市场有待进一步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较少,金融衍生品发展有限;还将面临与香港这一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协调问题
中国经济新闻网讯: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其中提出到2020年,要将上海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是中央在特殊国际经济环境下的审时度势之举,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提升中国金融实力具有深远意义。
外部机会
“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依托于各国的经济实力,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很可能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现在我国金融发展的态势却并未跟上经济增长的步调。”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室主任周宇认为,中央确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方向,从侧面显示出,强化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金融实力,将成为未来经济政策的重要倾斜点。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仍在感受国际金融海啸的惊涛拍岸,而中国金融系统所受冲击相对较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认为,这种彼竭我盈的大背景意味着,到处充满了中国金融的机会。
“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在历次危机中呈现出的脆弱和混乱,必然会导致各国金融实力的重新博弈。当其他金融市场对资金的吸引力相对下降时,也正是中国增强自身金融实力、提升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的机会。这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杨涛认为,国际性金融中心能够起到非常强大的金融资本积聚作用,加快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将有力牵引全球金融资源向我国不断流动。
“由于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中占比不多,目前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高,而推进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一旦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接轨,将会使得人民币国际间交易变得异常活跃,这将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显著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引导中国从制造业大国逐渐向金融大国和货币大国迈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骆玉鼎说。
内在要求
关于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提法曾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过,但该《意见》中提到“建立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种提法还是第一次。周宇认为,这一新提法说明政府已经开始了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上海要建设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依赖于成熟的人民币业务,这一前提和基础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周宇说,前几年上海曾提过建立以人民币产品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中心,当时的考虑是,如果上海像香港一样发展美元业务,不仅存在冲突,短期内也不具优势,而以人民币业务为依托可以避免竞争,发挥本币优势,但当时政策限制非本国居民使用人民币,因此人民币业务只能在国内范围进行。
“现在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把人民币业务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原来受到限制的大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业务就要逐渐放开,贸易项下人民币业务结算必然推动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开放,比如允许对外人民币借款,面向非本国居民和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这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系列措施对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会起到强劲推动作用。”周宇说。
“国际贸易一旦以人民币作为计价或支付手段的话,可以产生非常多的金融创新,金融交易也将大幅增加,这些都对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起到积极促进作用。”骆玉鼎说。
仍需努力
近几年上海金融市场发展迅速,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在全国金融资产总额中占有比重越来越大。截至2007年底,全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60.48万亿元,上海占6.94万亿元,约为全国金融总资产的11.5%。但骆玉鼎认为,和伦敦、纽约、东京这些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在很多方面都有待提高。
“强有力的监管、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健全的金融机构、完善的金融产品、大量的金融从业人员,是衡量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否成熟的五个方面。”骆玉鼎认为,上海金融市场监管虽然相对严格,但缺乏灵活性,比如股指期货、钢铁期货审批时间长,效率较低。除了资本市场外,尽管上海也建立了外汇交易中心、银行间债券市场,但场外交易市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上海的同业拆借利率SHIBOR与伦敦的同业拆借利率LIBOR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另外,在诸如非上市股权转让、产权交易等方面,在制度上仍需继续探索。
杨涛也指出,上海金融市场中的私募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比较缺乏,金融衍生品发展有限,甚至连期权、期货、掉期、远期四大基础产品工具的发展都还存在诸多不足。
“上海在发展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也将面临与香港这一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关系协调问题。”骆玉鼎说,“由于距离相近,上海和香港会存在一些冲突,比如跨国银行总部如果设在香港,在上海再设立的难度就很大。这些冲突都需要政策层面的协调,通过金融机构布局、市场布局、产业布局、产品试点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实现优势互补。在协调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合作双赢的局面,比如资本市场可以尝试沪港交叉挂牌,H股上市的股票同时也可以在上海交易所挂牌,这都将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更快实现对外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