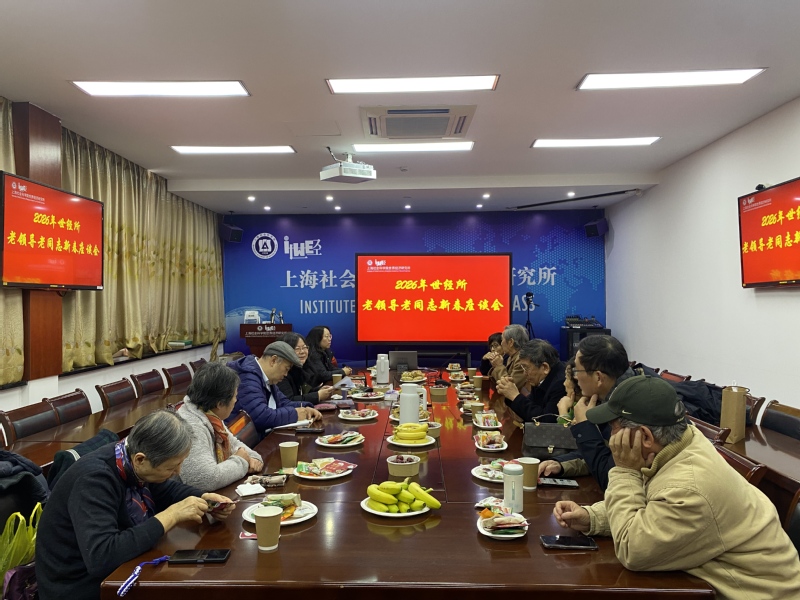2015年5月26日,在我院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由两家机构联合主办、世经所承办的首届国际经济论坛在我院举行。双方学者围绕“中美在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合作与前景”这一主题进行了三组对话与讨论。
在第一组对话中,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Jeffrey J. Schott和我院世经所研究员、上海自贸区研究协调中心秘书长徐明棋分别作了“中美贸易发展的前景与路径”、“从上海自贸区到亚太自贸区——中美在区域贸易安排上的互动”的主题发言。会议由世经所副所长权衡研究员主持。
Jeffrey J. Schott在发言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中美的贸易关系不断深化,双边贸易大幅增长,中国的关税率已经大幅下降,与发达国家相当,未来开放的重点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中美双方虽然各自都有顾虑,比如中国希望美国降低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美国希望中国更好保护知识产权、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但是这些磋商和谈判都在不断推进。中美BIT谈判意义重大,2015年9月中美领导人会晤可能对中美BIT产生突破性影响,中美合作的空间还很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愿为中国加入TPP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准确的信息。我们可以利用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经验来帮助打造中美更大范围的合作平台。未来中美双方的贸易关系可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快的话,2020年之前就可能实现,当然了它需要有大量的研究来支撑,要有很多的交流和讨论,我们许多专家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徐明棋认为,全球贸易增速虽然在危机后有所反弹,但仍没有回到危机前水平,全球贸易体系则出现了新的变化,很多国家在用区域的和双边的贸易协定获取更好的外部条件。虽然WTO想推进多哈回合谈判,但收效甚微,而且WTO的成员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的措施,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欧盟都有雄心壮志,想要用双边协议以及多边协议来制定一个国际贸易新体系,TPP、TTIP是很好的例子,就是所谓的21世纪综合的贸易协议。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利用自贸区来进一步检测开放的一些方法,来加速与贸易伙伴的谈判,推进中美BIT谈判,来促进贸易以及投资的自由化。中国也意识到,综合的、高标准的贸易协议是不可逆的趋势,所以中国也是准备拥抱这个趋势。中国的自贸区探索是成功的,未来会拓展自贸区的一些经验,进一步打开市场采纳国际标准,积极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在会议的第二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Caroline Freund和我院世经所国际贸易室主任沈玉良研究员分别作了“区域贸易监管平衡及其经济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亚太自由贸易进程”的主题发言。会议由世经所副所长姚勤华研究员主持。
Caroline Freund认为,区域贸易自由化中监管的融合非常重要,每个国家在监管标准上是有差异的,对于不同的市场这种标准差异可能为企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她以汽车产业为例分析了监管融合有利于汽车产业的发展,有利企业发货规模效应,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推进区域贸易的发展。分析指出如果监管标准统一,欧美之间的汽车贸易将能够增长20%。关于TTIP欧盟的目标是希望欧盟和美国之间有更好的监管兼容性,美国的目标是TTIP可以设立高标准,这个协议基本上就是关于市场的融合以及先行者的优势,80%预计的收益来自于非关税壁垒的调整。
沈玉良在发言中提出,NAFTA类型和GATS类型服务贸易规则的差异关键在于标准的不同,在整个跨境服务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差别上,GATS框架里面没有包括国际投资,而NAFTA类型用负面列表的方式,美国很多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也都采用NAFTA类型,包括TPP、TiSA。这种形式为中国参与新规则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沈玉良研究员认为中国需要在推进亚太自贸区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需要加速国内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调整,通过试点和全关境两种方式开放服务业,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相关规则也需要不断完善。中国为世界提供巨大的服务市场,亚太货物贸易的互联需要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的互联。中美在共同推进亚太自贸区的发展上具有合作空间,双方共同面临的问题包括服务贸易的政府治理,网络安全的技术、制度和跨国合作等。
在会议的第三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R. Lardy和我院世经所副所长权衡研究员分别作了“服务贸易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经济新常态下上海服务经济新转型与新开放”的主题发言。会议由徐明棋研究员主持。
Nicholas R. Lardy在发言中分析了服务贸易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他指出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当时服务行业是很欠发达的,服务领域被认为是产能不高的一个领域,只占了整个产出的20%。但是随着80年代、90年代的开放,服务领域有了很大的发展,到2001年,服务领域的占比就达到了40%,差不多翻倍。在之后的十年当中,服务领域实际上增长的并不是很多,主要由三个因素导致的:一是在2000年初,人民币持续贬值给制造业的产品提供了补贴,压抑了服务业;二是该时期中国的金融压抑严重,也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资金更多流向了制造业;三是中国经济政策对能源需求的提高也刺激了制造业而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而近几年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中国的服务业增长速度超过了GDP增速,同时服务领域的开放也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从全球化角度,Lardy认为,推动私营部门的竞争,将更多行业向私人资本开放,比如说电信等服务业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这方面已经有一部分的进展,但还比较有限,所以服务行业的前景、潜力很大,能够提升产能、生产效率、提升资本的回报率。而这一过程需要通过开放市场实现,既要对国内的公司开放也要对国外的资本开放,让私营部门取代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是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选择之一。
权衡在发言中指出,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增长速度进入中高速,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以及新的增长动力的转化,包括要防范一些新的风险。权衡研究员认为增长趋势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的本质,就是赶超的增长态势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增长率下降并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像发达国家这样进入一个增长的均值状态,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真正的赶超发达国家,才刚刚起步,这样一个刚起步的赶超不可能在短短的三十多年就停下来。从横向比较看,未来的10年左右能不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非常关键。但是,中国的赶超速度在下降,主要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及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的改变对中国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等等,这些也抑制了过去的高增长的方式。另外,中国政府职能也在转型,在这些要素影响下传统的要素驱动增长的动力正在衰减。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上海率先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经济的发展,早在五年前上海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上海服务经济的开放领先于全国。未来非常重要的是如何使得创新驱动成为服务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带动服务业发展。上海市政府通过了关于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计划,在2020年上海全面建设四个中心的时候,科技创新中心一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会上,世经所金芳、赵蓓文、黄烨菁、孙立行、孙震海等研究人员围绕会议议题积极参与提问、评论与互动。大家对中美在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中合作及前景总体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中国目前的正在进行的国内改革以及经济的转型实际上都是在向国际高标准靠拢,这也是与美国提出来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相一致的,因此中美具有坚实的合作基础和广泛的合作空间。TPP的签订可能不会产生不平等,这个问题需要从福利的角度全面考虑,相反也有可能刺激中国进一步的开放。中国打开服务领域可能会导致大量的资本净流出,但是服务领域开放的同时也会吸引很多外国投资进入到中国,比如说电信业、金融服务业等都对外商投资都有很大的潜力,因此开放服务业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要全面分析,很可能是净流入。美方学者对人民币国际化持肯定态度,希望人民币能够进入SDR篮子,这样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对全球也有正面影响,美国不希望美国使用一票否决权。最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希望今后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为共同建立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