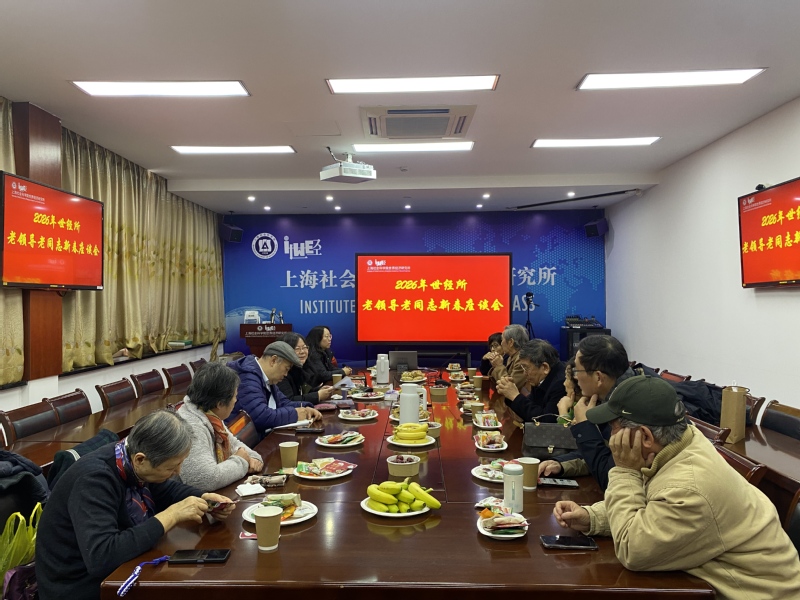当前国际体系的性质与中国的互动
冷战结束后的过渡体系,是美国主导、西方占有全面优势并掌握制订游戏规则权力的体系。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前苏东集团的解体,以美苏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两极国际格局终结,国际体系进入了一个从两极向多极逐渐过渡的阶段。之所以说是过渡,是因为,虽然美国仍然是这个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相对于欧盟、中国、俄罗斯以及印度等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发展而言,这种力量对比正在缓慢地向各方相互均衡的方向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各种国际制度在当前国际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当前乃至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际制度对于推动或制约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什么是国际制度?按照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指“国际行为体在国际关系某些特定领域中在认识上趋于一致的一系列隐含或明确的原则(principal)、规范(norm)、规则(rule) 和决策程序(decision making procedures)。”[1] 具体而言,目前不同领域的国际组织通过各自的议事规则和程序所制定和达成的协议或决定就是国际制度的具体体现。例如,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有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及北约的形式,有核不扩散条约、禁雷公约的形式,有根据安理会决议所作出的对某些国家实行制裁、限制特定产品或原料出口的形式;而在经贸领域,则主要体现在功能各异的国际金融和贸易组织以及相关的国际协议,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它们各自的议事规程和条约;在其它一些领域也存在大量的国际法和国际规范来协调国家间的交往与合作,如规范外交礼仪和交往规则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确保各国和平利用人类自然资源的联合国海洋法、南极条约体系等,以及为方便各国正常交流所制定的一些国际通用的度量衡制度,如电器的频道制式、电源电压标准、集装箱规格以及目前尚未完全形成国际统一标准的即时通讯标准等。
当然,这些国际规范的制度化程度是有差别的,有些是成文的、以国际法形式出现的正式且具有相当约束力的规章制度,有些则是不成文的、非正式的默契与合作,也就是说,国际制度可以是国际组织和大国会晤的决议及其产物,是一种真正的组织安排,由国家之间的协议或条约组成,也可以是私下交易和没有公开组织的活动的结果,仅仅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配合默契的过程。从目前来看,不管是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正式国际协议和规范,还是那些无形的默契行动,其主导权基本上被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所掌控。例如,作为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代表,联合国从建立伊始到今天,无论是最早的联合国宪章条文的制定,还是此后一系列涉及国际安全事务的重大决议,包括联合国秘书长人选的确定,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首肯,就肯定无法付诸实施。而作为国际金融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无论在组织结构还是运行机制上,受美国影响和控制的程度更甚。最典型的就是IMF的加权表决制度,即成员国的投票权是与其份额大小成正比的,而美国一直是该组织中占有份额最多的国家,其拥有的投票权也最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发挥其影响,是通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董事会中的代表,通过这些组织的所在地和员工,同时也由于两家组织都要讨美国政府和议会的欢心。美国拥有绝对力量(与其他国家相比),能使该组织向其负责”。[2]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不同的国家,对于国际制度的遵守程度也不尽一致,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经常按照自己的利益取舍,安排一些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和决议文本,在不如其意的时刻则违反原本由它自己作出的制度安排,但这种行为如果保持在一定限度内,或是并不与其他重要国家的核心利益直接冲突,其它国家纵然心有不满,但往往也不会因此而公然与美国为敌。只有国际制度的参与者在规则和程序上发生根本分歧,他们对规则的违反或破坏也不受任何惩罚甚至批评时,国际制度的效力才真正受到质疑。
由于冷战是以非战争方式而结束的,因而当前的体系与冷战体系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种过渡的性质对中国也带来积极促进和消极制约两方面的影响。从共同点带来的积极意义来说,由于没有体系战争的冲击,绝大部分国际制度保持了延续性,这为推动国际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增强了国家间交往的预期,降低了国际合作的交易成本。这在国际经济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这对于中国更快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当然,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大多数国际制度更多地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原有国际体系既得利益者的偏好,中国在接受国际制度时必然是有所选择的。过渡阶段产生的另外一种消极影响则体现在,所谓的“冷战思维”经常有意无意地影响着强国对外政策的出台,这一点同样在美国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那么,这种“冷战思维”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根据国内目前一些学者的归纳,其根本实质就是传统国际政治中以极端的权力追求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来看待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一种思维模式。[3] 由于美国成为冷战中最大的获益者,美国国内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相当一批人更加相信他们在冷战时期采用的各种针对前苏联的政策和措施的有效性。为了确保冷战后美国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他们就总是有意无意地会倾向于利用冷战时的政策思维来指导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当然,冷战思维并非美国专利,这种过分注重安全需求,戴着意识形态眼镜的人在中国同样存在。不管存在于哪一个国家,在一个经济相互依存日趋紧密的全球化时代,这种思维必然不利于大国间的国际合作。
当前国际体系与冷战体系最大的差别除了结构上的变化以外,对于国家发展具有最大影响的就是日趋紧密的经济相互依存。虽然学术界对相互依存的内涵始终存在争议,[4] 相互依存也并不自动带来国际合作与和平,但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同意:相互依存的确会促进和有利于合作与和平,[5] 除非国家认为这种相互依存带来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会被他国用来损害自己的利益。对中国而言,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化是与现阶段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家基本发展战略一致的,它有利于中国更好更快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也会出现理论家们指出的不对称相互依存问题,目前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结构中,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在中国出口商品中占有的比例仍然偏多,而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品则在中国进口商品中占有较大份额,这就说明中国在与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相互依存中所具有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更高,这无论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位置还是自我创新能力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当前国际体系的格局是: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也无法完全控制其它大国,而其它大国或大国集团能牵制美国,但也不可能完全遏制美国。从国家的综合国力来看,现在的美国毫无疑问处于国际体系的顶端,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霸主。因为无论是以往的罗马帝国、中华帝国还是近代的大英帝国,要么只是区域性霸主,要么也只是商业和海洋霸主,而不象现在的美国,无论在哪个领域都堪称世界第一。美国的GDP总值长期以来高居世界首位,以这种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美国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军费开支更是不断增长,目前已经占全球军费开支总和的四成还要多,相当于它之后差不多十五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最重要的是,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仅占其GDP总量的3.5%左右。如此巨大的压倒性优势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空前的,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的,“付出巨大代价成为世界第一是一回事,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仅仅付出了低廉的代价才是惊人的”。
虽然当前美国已经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并不能像历史上类似的霸权国那样指挥和控制其他大国,相反,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能够在某些情况下对美国的行动有所牵制。这一点在经济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在政治领域,这种牵制作用则取决于利益对于各国的相关度,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认为某种利益对其具有关键意义,即使美国为了实现这种利益采取的行动对其他大国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其他大国能产生的牵制作用也弱。这一点在美国不顾其大多数欧洲盟国反对而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一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美国眼中,伊拉克可能私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暗地里支持国际恐怖组织,而这些正是现阶段美国所认定的对其国家利益最大的威胁,因此即使得不到盟国的全部支持,美国仍然会采取单边行动。但在经济领域,一方面由于美国与其他大国和大国集团的实力对比不像军事力量对比那么悬殊,更重要的是,经济领域里的争端本来就不太可能利用强制力量来解决,因此,美国所受到的各种牵制与制约就更大。例如,近年来美欧之间的经贸摩擦逐渐增多,强度也日益加剧。这是与欧盟内部一体化水平的提升及欧盟扩容密切相关的,随着欧盟从整体上在多个领域超过美国,欧洲必然不再心甘情愿地充当其在冷战期间扮演的角色,这从美欧之间近年来在农产品、钢铁、航空以及市场准入等问题上不断发生的争端可见一斑。随着欧盟成员国的进一步扩大、其一体化程度的进一步增强以及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的进一步加强,类似的经贸争端也将更加频繁。
相对于国际政治体系,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具有更强的规范性,因而其作用大于国际政治体系,后者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国际关系所描绘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经济体系的两大支柱,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都有各自的正式国际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来保障正常的运转。虽然这两大机构目前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受到许多批评和质疑,但作为管理和协调国际金融、货币事务并向成员国提供资金融通业务以及协调全球贸易事务的最重要国际机构,IMF和WTO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举足轻重。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其中以及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6] 它们在全球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将更加明显。而作为国际政治体系集中体现的联合国,虽然自成立至今也有半个多世纪,但相对于功能性色彩更浓的国际经济事务,政治事务由于涉及国家主权等敏感领域,国际合作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都大打折扣。最关键的是,虽然联合国宪章中有第七章这样的强制性条款,但由于存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使得强制条款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相对于国际经济合作的范围和程度,国际政治合作仍然是相当有限的,传统国际关系所强调的“安全困境”并未消除。
虽然国际政治合作比较脆弱,但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当前国际经济体系具有更强的规范性是有利的,因为中国首先是从经济上崛起,保证了中国可以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例如,中国从成为WTO正式成员国之后就全面参与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的进程,这也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第一次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这不但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这对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均衡发展状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近年来多边贸易规则的进展更多地倾向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发展中国家分享的收益太少,而承担的调整负担太多。作为一个国民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中国参与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建立和完善,本身就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战略性行动。中国对多哈回合谈判的基本立场是:新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应当有利于建立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平衡。同时,中国政府认为,及时、妥善解决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实施问题,对恢复和增强发展中成员在新一轮谈判的信心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纺织品和反倾销等问题上,发达成员应拿出谈判诚意,并采取实际行动改善发展中成员的市场准入条件。[7] 中国的这些立场和观点并得到了世贸组织成员,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支持。除了在香港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之外,第六届亚欧财长大会以及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都在中国召开,这些都说明中国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创制中来。
中国应当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大国
如果说十年前还有人对中国能否崛起存在怀疑的话,现在无论在政界还是学界,这已经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崛起已经是不可遏止的必然趋势,关注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西方舆论中一直存在“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中国威胁论”有多种版本,从发展历程来看,从最开始的中国军事威胁,逐渐发展到经济威胁以及文化威胁。不管是那种版本,这种观点基本的看法就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当这种不满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中国就会凭借自身日渐强大的力量挑战现存秩序,从而威胁到国际和平与稳定。著名现实主义学者吉尔平的一段话经常被人引用来描述这一过程,“现实主义的不平衡增长规律意味着,随着一个集团或国家实力的增加,该集团或国家就将受到诱惑,产生加强对其周边环境控制的企图。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感,它也会力求扩大它在政治、经济以及领土方面的控制;它还将试图改变国际体系,使之符合其一系列特殊利益。”[8] 这种观点最常见的论证方式就是把中国与国际关系史上那些向霸主国进行挑战的国家来比较,从而来说明中国强大后必然威胁到现存国际秩序。[9]
相对于这种从传统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间对权力争夺来预测未来的方式,目前欧美学界和政界已经有不少人从更为全面的角度,即不单纯从政治和军事这些传统的所谓“硬力量”来评估中国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开始注重分析中国文化和思想这种“软力量”因素在中国对国际体系发挥影响中所起的作用,从这些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大多对未来持不确定的态度。[10] 也就是说,中国强大后到底会走修正主义路线还是继续维持现状,不能仅仅像传统的现实主义者那样简单地与历史类比,而必须具体分析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来判断。[11]
虽然国际上对中国迅猛发展提出的挑战仍然存在各种疑虑,但正如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近年来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指出的,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世界形成威胁,恰恰相反,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的机会远远大于挑战,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中国也将承担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国际义务,成为现存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大国。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最明显的例证从中国周边国家十年来的稳定发展可以看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很多国家希望日本承担起它作为亚洲经济领头羊的责任,维持汇率稳定,但日本为了一己私利,不但没有维持日元汇率,还促使日元贬值,导致日本产品出口猛升,使得泰国和印尼等国的形势雪上加霜。而中国此时正是从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承担的义务出发,为了保证整个地区经济的平稳发展,维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虽然中国的出口因而受到很大损失,但却赢得了东盟国家的一致赞赏与肯定。之后,随着中国与东盟“10+1”机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行,从2002年开始,双方正式开始就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双方的经济合作走上了一个新台阶,东盟各国自金融危机后十年来,已经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整个九十年代经济一直处于停滞阶段的日本,近几年来也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从中国从日本的大量进口)而获益匪浅,即使是在政治上顽固坚持强硬路线的小泉纯一郎,也在多个场合公开表态,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是机会而不是威胁。此外,中国周边的两大邻国—俄罗斯和印度—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而获得越来越多的发展良机。其实,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从十个方面所指出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由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需要和国家利益决定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曾经一度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的小布什政府,也已经逐渐改变了态度,充分认识到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共同战略利益大于双方之间的分歧。以前助理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在2005年9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演讲中提出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概念为标志,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开始向相对理性务实的方向转变。按照佐利克的看法,国际体系帮助中国获得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强化这个体系。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实现“走新兴大国从未走过的道路”的目标。而美国要做的就是“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2006年2月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3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引用了这句话,可见,这个提法已经成为现阶段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的一个基本概念。当然,正如佐利克在演讲中也指出的,提出“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并非意味着双方在所有问题上都没有分歧,而应在保存共识的基础上,部分地解决分歧,“处理分歧可在更大的框架下完成,即各方都承认,有关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可使各方共同受益,维护这个体系符合各方的利益”。
虽然中国与美国共同存在的战略利益大于双方的分歧,但同时美国对中国崛起始终存有疑虑,担心中国进入现有体系后会改变这种有利于美国的体系。美国希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前提是不挑战美国在此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从佐利克的演讲中也可以看出来。无论是他提到的经济领域中的贸易逆差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还是政治安全领域中的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反恐问题,都是美国更加关注的利益之所在,而他所提到的绝大多数解决方式就是要按照美国所界定的标准来进行。
实际上,中国在国际体系建构上也有自己的战略考虑,这就决定了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将长期存在。中国在2002年首先提出了超越单边安全,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互利合作来寻求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而且中国正是本着这样的新安全观开始尝试在区域层次上建构新的国际机制,这是由中国自身的地位以及现阶段国际格局所决定的,上海合作组织就是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而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建构“和谐世界”新理念,进一步升华了中国对于未来国际体系秩序的构想,它将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新发展观以及新文明观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国所强调的在国家之间保持和平,人民之间保持和睦,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合作共赢,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的外交新宗旨。
而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于国际体系当然有其自身的战略利益。克林顿政府时期提出的美国国家战略是以安全、经济和民主为三大支柱,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用积极手段参与国际事务,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美国的价值观和市场经济模式,以此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911事件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认为美国本土不会受到攻击的“美国例外论”观念,小布什执政时期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相对于克林顿政府时期注重经济而言,就更加注重安全问题,面对基地组织的挑战,美国把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视为其最大的威胁。“我们国家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在于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为了对付这种与传统的国家间威胁不同的挑战,虽然美国一方面仍然认为要保持国际合作,尤其是大国间的合作,但同时却提出了“先发制人”打击敌人的战略,“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果断地单独采取行动,行使‘自卫权力’,对恐怖主义分子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如何确定“敌人”呢?这就完全按照美国自身价值观的判断,所以美国认定伊朗和朝鲜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针对美国,就是所谓“无赖国家”,并一直向它们施加压力,甚至威胁使用武力。可见,美国这种处理国际事务的理念和方式还是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的。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选择
目前的国际体系可以大致分为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安全体系,价值和意识形态体系这几大类,从当前国际格局的形势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由于中国目前上升最快的是经济力量,而国际体系中无论是制度化程度还是相互依存的深度与广度,也首推国际经济体系,因此可以明确的是,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融入国际体系的重点仍然是国际经济体系,但对中国最大的压力也将来自国际经济体系。
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一方面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提倡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却同时也是该组织唯一没有得到普遍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成员国,这就直接导致中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世界上受到反倾销诉讼案件最多的国家。中国当初为了打破中美之间在入世问题上的僵局,曾经做出妥协,即同意在加入WTO之后的15年内,美国可以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实际上就维持了中国入世前相对不利的反倾销机制,而这就越来越多地成为欧盟与美国启动对华反倾销程序,而按照原有的第三国替代机制,往往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倾销判定经常会成立,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此外,近几年比较大的来自国际经济体系的压力还有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美贸易逆差增大以及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应该说,这些问题有些与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它们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制度化水平的完善而不断完善,有些则并非仅仅是中国的责任,如中美贸易逆差增大,其中很重要的因素与美国的贸易政策有关。美国一方面高喊自由贸易口号,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多地在贸易政策中加入政治色彩,除了众所周知的限制高技术产品贸易之外,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依据是国内立法,也就是说,美国是用国内标准来判断国际贸易,这种单边主义政策必然导致美国国内利益团体会出于一己私利而在国际贸易中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如劳联-产联就经常为了维护自己的选票利益指责中国的纺织品在美国倾销。
不管是哪一种具体的国际经济摩擦,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贸易总体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自国际经济体系的压力将只会增多而不会减少,实际上,这从反面证明中国的综合实力在不断提升,因为如果国家又穷又弱的话,它与国际经济体系的互动程度就很低,当然产生的国际经济摩擦也就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应该对解决这类国际经济摩擦充满信心。从长远发展而言,要完全解决国际经济摩擦是不可能的,但从这些经济摩擦的本质来看,它们是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过程中与国际经济体系互动时必然出现的现象。从宏观层面上讲,要顺利地应对这些来自国际经济体系的压力,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尤其要重视对研发力量的投入,使创新能力上升到国际水平,把战略重点从单纯的价格竞争逐步转移到高层次的质量竞争上来。
以联合国等一系列相关国际组织为体现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不具备改造的能力。目前的联合国体系是在二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无论是议事规则程序,还是重要的权力机构组成,仍然基本反映的是二战结束时的状况,它与当前国际社会的发展形势的确存在一定的脱节,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强的原因之一。正如在上文所指出的,与其它国际制度一样,联合国体系的一系列游戏规则仍然更多地反映和有利于强国,尤其是美国的意志和利益,因此,联合国可以迅速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做出反应并组织国际力量来恢复原有秩序,但遇到类似美国入侵格林纳达以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局面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虽然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对这种状况并不满意,尤其是2003年美国不顾其大多数欧洲盟国反对而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使传统的跨大西洋同盟出现裂痕,美德、美法关系都因此受到损害,美国更是在2005年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提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四国方案时只表示支持日本、印度和巴西,将美德矛盾公开化,而此后的“黑狱”事件使双边(美国与美国所称的“老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陷入困境,虽然此后法德都竭力弥补这种受到损害的关系,但可以肯定地说,未来的跨大西洋同盟将不可能回到冷战时的那种状态了。[12] 美欧关系的演变对于未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在短期内它还不会形成直接的后果,而且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间接的。但如果国际政治体系由于某些特定事件发生重大改变(如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则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从2005年联合国改革日本争取入常的案例来看,中国在现阶段最有效的策略是依靠多数,利用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在未来应该大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关系,这对于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而在以军事实力为体现的传统国际安全体系中,虽然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强劲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大大提升,军事现代化水平有了长足进步,但与美国相比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长期内还不具备与其对抗的能力。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目前的国际安全体系中,非军事实力和非传统安全的因素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无论是被美国列为其最大威胁的恐怖主义,还是近年来日益加剧的环境恶化、毒品走私、传染病扩散等,都对各国的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些威胁造成的损害在有些时候甚至远远超过传统的战争对国家造成的损失。如2005年8月登陆美国南部的卡特里娜飓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造成美国受灾地区的上千人死亡(相比而言,从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截止到2006年6月中旬的三年多时间,美军的阵亡数字才达到2500人),百万人无家可归,而且由于飓风淹没了众多炼油工厂,切断了石油管道的电力供应,摧毁了石油钻井设备,直接影响到美国乃至世界的能源市场,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也不断飙升,原油价格创下新高。根据权威经济学家的估计,飓风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300亿美元,重建工作所需的资金也超过911事件带来的损失。布什也承认,美国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从灾难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可见,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面对一场自然灾害时却如此脆弱,这固然有在美国国内饱受指责的官僚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它说明,一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飞机和航母,在面对卡特里娜飓风这样的自然灾害时,这些武器显得毫无意义,它们与一堆破铜烂铁没有差别。同样,无论是这几十年来在全球不断蔓延的爱滋病,还是近几年才受到高度关注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和非典型性肺炎(SARS)这些在国与国之间迅速传播的传染性疾病,依靠传统的军事解决手段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只有通过不断深化公开公平的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人类社会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与中国所倡导的多边国际合作思想是相吻合的,中国这几年来也积极参与并不断扩大了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如分别同巴基斯坦、印度、泰国海军组织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联合演习,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互通防控各种传染性疾病的重要信息,参与相关的合作抗击传染性流行疾病的国际会议,为相关国家提供所需的帮助。积极参与国际重大自然灾害的救险工作,如派遣中国国际救援队到印尼海啸灾区以及伊朗地震灾区等实施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可以说,中国近几年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有所作为地发挥了自身的影响,这条道路也应该是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扩大国际影响,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渠道。
至于在传统的国际安全领域,从目前来看,中国唯一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是在地区体系内。在实践中,中国正在用新安全观与和平发展的思想通过国际合作和一些制度性安排来影响和塑造地区体系的发展,这方面典型的例证是上海合作组织,从目前的发展趋势而言,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在国际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的时期,上海合作组织从正式成立到今天,在指导地区性多边反恐合作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与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路线,单纯依靠军事行动实施“反恐”不同的是,中国所积极推行和倡导的正是以新安全观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在实践中成功地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安全机制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当然,这方面的活动还仅限于地区范围内,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不能与美国直接对抗。[1]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2] 耐革尔•伍兹 安瑞塔•纳利卡,“治理与责任的限度: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2年第4期。
[3] 张晓明对此的界定是“过分强调国家间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对立”,“过于强调国家的政治与军事安全”。张晓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390,392页;时殷弘等则界定得更为明确,即认为“冷战思维”表现为五项基本内涵:(1) 追求绝对安全,而非满足于相对安全;(2) 将准备对付最坏情况当做制定国策的主要或惟一出发点;(3) 不能或不愿设身处地似地理解对方的利益、情感和安全担忧;;(4) 以“自现预言”的方式制造敌人和对敌战略规划;(5) 用“挑战史”和“谋霸史”来牵强地附会当今和未来。时殷弘 陈然然:“论冷战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6期。
[4] 关于对“相互依存”内涵的分析,最著名的当属基欧汉与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中所进行的阐述,该书第一版是1977年,此后两位作者根据时代变迁引起的一些新的变化进一步丰富了它的内涵。最新版的中文版可见(美)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实际上,在该书第一版问世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相互依存现象,如Edward L. Morse, “The Politics of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3:2(1969), pp.311-326; Richard Rosecrance & Arthur Stein, “Interdependence: Myth of Reality?”, World Politics, 26:1(1973), pp.1-27; Peter J. Katzenstein,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Some Long-Term Trends and Recent Chang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9:4(1975), pp.1021-1035; Richard Rosecrance, A. Alexandroff, W. Koehler, J. Knoll, S. Laqueur & J. Stocker, “Whither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1:3(1977), pp.425-471.
[5] Paul A. Papayoanou,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1:1(1997), pp.113-140; John R. Oneal & Bruce M. Russett,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
[6] 目前IMF有184个成员国,而WTO有150个成员国(不少国家已经申请加入但仍在等待批准,如俄罗斯)。
[7] 根据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2005年12月WTO香港部长级会议的发言,中国参与多哈回合谈判的具体目标包括六项:(1)立即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免关税、免配额的待遇,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的待遇,以便在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照顾大多数;(2)力争在香港会议期间就棉花等问题作为阶段性成果达成共识;(3)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中支持双系数瑞士公式,且两个系数之间应有足够的差距。同时应保留为发展中成员所规定的灵活性;(4)为促进发展中成员更多地参与世界服务贸易,在谈判中应在发展中成员关心的部门和出口形式方面给予切实照顾;(5)进一步澄清和改进反倾销等规则方面的现有纪律,有效防止滥用反倾销措施、加强透明度,减轻中国这个世界反倾销最大受害者的损失程度;(6)中国作为新成员的特殊关注必须得到有效解决,要根据2004年7月框架协议的规定,切实给予中国等新成员特殊和差别待遇。
[8]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7页。
[9] 这种论证方式最典型的例证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则以理论性更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为标志。具体分析可参见(美)理查德·伯恩斯坦 罗斯·芒罗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 Thompson, “Power Transition, Challenge and the (Re)Emerge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29:3(2003), pp.315-342; Jean A. Garrison, “
[11] 关于中美之间谁更像修正主义者的讨论可参见LanXin Xiang, “Washington’s Misguided China Policy”, Survival 43:3(2001), pp.7-23; David Shambaugh, “China or America: Which is the Revisionist Power”, Survival 43:3(2001), pp.25-30. 而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则通过他设定的五个标准来判断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现状国家,根据他对中国参与各种国际制度的详细分析,他认为,中国并非一个修正主义国家。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12] 近年来反思跨大西洋关系的文献如Francois Heisbourg, “US-European Relations: From Lapsed Alliance to New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1:1(2004), pp.119-126; Edward Rhodes,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Righteous: Understanding the Bush Vision of a New NATO Partnership”,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3:1(2004), pp.123-143; Erik Jones, “Debating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Rhetoric and Real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80:4(2004), pp.595-612; Dana H. Allin, “The Atlantic Crisis of Confid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0:4(2004), pp.649-663; Michael Cox, “Beyond the West: Terrors in Transatlant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2(2005), pp.203-233; Simon Serfaty, “Terms of Estrangement: French-American Relations in Perspective”, Survival, 47:3(2005), pp.7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