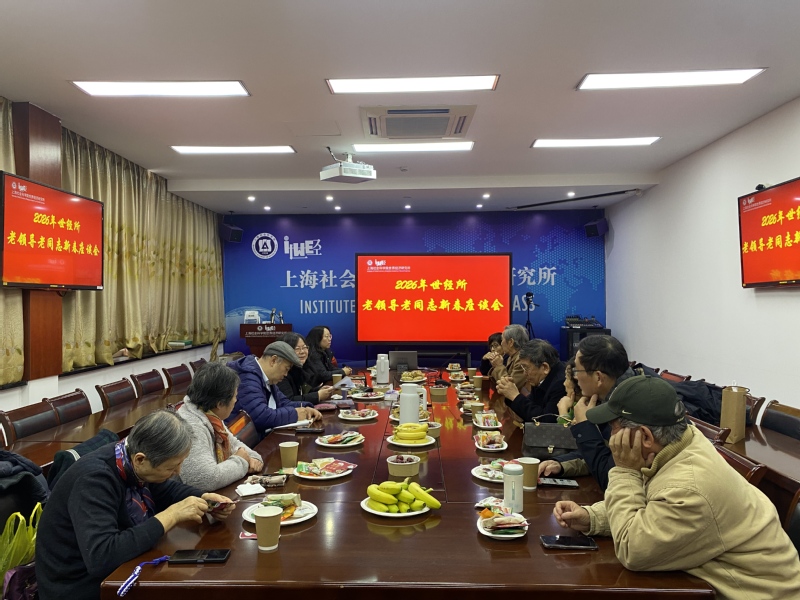国际服务外包是目前企业国际化行为中的一个重要模式,是跨国公司基于自身归核化战略实现企业对外筹供战略的方式之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上除了源自于成本导向的商业获利之外,外包双方之间因信息流动构成的接包方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外溢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外延影响。这对中国相关企业开放条件下的技术积累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将带来怎样的作用,论文就此展开分析。
一、 国际服务外包的理论与实践——宏观效应与产业发展动向
从全球市场发展态势看,服务业外包市场相比制造业外包呈现出更迅猛的扩大与创新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发展,(为代表的)服务外包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相当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服务外包市场的增长点。现有的理论者已经阐述了服务外包在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和生产网络化层面上带来的效应,构成外包的宏观经济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梳理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全球服务外包的最新动向,对服务外包的技术效应的深入研究作一个铺垫。
1.文献综述
企业承接外包对企业经营和资源管理的带来的效应是目前外包微观效应问题的重点,以企业资源论、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和战略理论(Strategic Theory)为出发点的研究主要关注外包对企业成本和效率的影响。产品内分工的理论假设则是国际外包宏观效应的一个重要视角,有学者基于国际服务外包的经济利益来源和成本约束,探索了国际服务外包对产业在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生产网络化等层面上的宏观效应(卢锋,2007)。国际外包对于接包方的多重效应问题,现有的研究观点主要有:首先,在发达国家国际外包层面上,有研究提出了外包的收入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即技术工人的收入渠道间接地影响接包方国家相关产业的技术要素的积累,长期而言对产业升级带来正效应(Freestra,1998;Freestra & Hanson,2005)。其次,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技术效应相比,外包活动构建的技术发展动力机制更多地受市场因素影响,这是外包基于合同/纽带的微观模式所决定的。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包,发包者把接包企业作为制造环节和服务特定功能的供应链主体的同时,也会给予接包方在质量控制、工艺、技术标准与企业内部管理方面的培训,这个过程给发展中国家企业带来技术外溢效应,对承接方企业短时期内达到国际市场产品(服务)标准的影响强度更大。还有国内学者结合我国服务外包的动态发展,指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带动接包企业与发包的跨国公司之间联合研究和开发的积极影响,作为技术相对后进的接包方企业获取了其自身短期内难以自主积累的知识和技能, 转化为商业敏感技术和知识,客观上“培育”了竞争对手(刘志彪,2007)。第三,当前中国承接服务外包是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契机,应对战略是企业必须积累创造性资产,逐渐向价值链的高端服务发展,这成为服务外包活动中提升长期技术竞争力的关键路径(谭力文,2006)。
2. 服务外包的创新动态——“技术型”服务外包的兴起
当代全球服务外包一个显著的趋势是服务外包与新技术手段的充分融合,目前发展最活跃的两类服务外包分别是信息技术外包(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 简称ITO)和商业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ing Outsourcing, 简称BPO)。ITO 和BPO均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外包,运作方式高度依赖信息和网络技术以及相对复杂的组织管理能力,因此对于接包方企业构成一定的“技术门槛“,下表(表1)对这两类外包的特征和微观机制所作的对比分析,能够使我们对两类技术密集型外包的技术手段以及运行过程中双方企业的技术关联有一个初步认识。
表 1 信息技术外包和商业流程外包的特点
信息技术外包(ITO) | 商业流程外包(BPO) | |
外包内容 | 企业部分(或全部)信息管理系统,包括数据转换、数据库管理、技术支持、内容开发、应用软件开发、系统管理等 |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呼叫中心、金融和会计事务等商务或者业务流程 |
技术平台 | 与软件技术(主要是应用软件)融合的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技术 | 借助IT手段(电信和数据网等)以及其他流程管理技术和最优化技术 |
发包方企业的外包目的 | 通过节约和降低成本寻求效率的提高 | 通过将优化企业的商业任务和业务流程的经营,实现商业结果的改善。 |
外包发包方和接包方的合作特点与交流方式 | 接包方服务于发包方企业信息处理、加工与网络技术相关的业务环节,双方交流限于价值链局部领域。 | 接包方负责发包方企业的商业结果,介入企业内部管理和市场战略,信息交流呈多元化特征。 |
这两种类型的外包活动不仅高度依赖网络和其他新兴技术手段,而且对双方信息与知识沟通以及相互反馈而言具有比制造业更加显著的特征。对发包方企业而言,外包所转移的信息管理和业务流程管理包含了大量企业战略意图和内部资源管理上的信息;对接包方企业而言,基于其专用性资产的服务技能在与客户特定需求的结合过程中,使自身的知识库积累也获得积极的动力。因此,相比制造业外包对加强彼此知识库和综合资源管理信息的沟通和互动提出更高的要求。除此之外,服务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微观运作和企业关联机制包含更多的隐性知识,是企业外源性的知识和信息库中重要的一部分。另外,在BPO活动中,由于企业双方推进合同内服务功能需要深入到企业业务流程以及信息管理过程的内部,对企业业务的总体性参与以及动态调整的渗透要比ITO活动更为紧密,从而引发更为复杂和多层次的隐性知识流动。
二、 服务外包活动内供需双方的信息和知识流动机制
前文分析了两类新兴服务外包的特征使我们对服务外包的运作过程中双方的技术关联有所了解。这个关联的本质是企业内部管理和市场战略内涵的各类显性和隐性知识的相互叠加,这个机制成为外包接包方开放型创新要素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创新孵化与成果市场化的动态源泉,是我们解读外包对接包方企业长期技术效应的一个出发点。
1. 服务外包过程中的信息与知识纽带
围绕着特定外包服务内容的“委托-代理”关系,外包的供需企业最基础的信息交流主要围绕着特定服务的质量和技术要求,包括一揽子技术标准、诀窍,在此基础上,以综合性的业务流程管理为代表的外包则是基于企业综合了市场开拓、资源管理和创新管理的价值链的“模块化”和外部筹供。在外包过程中,这些基于特定企业属性的信息直接或者间接地传递到与接包方的合作过程中,成为各类正规与非正规知识和信息在外包运行过程传播与反馈的“原点”。由于服务产业价值链的要素结构更加倚重人力资源,这些信息依托人员交流而构成隐性知识的流动和扩散,以正规和非正规交流强化知识在企业内外主体之间的相互反馈,对跨国外包中的多级参与主体(包括一级和二级接包企业)都带来信息与知识的外部性效应。
这个过程包含的信息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有关最优化管理机制、质量标准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标准,是融合大量专业知识和诀窍的正规和标准化的信息,属于显性知识[1],贯穿于外包的准备、运行和后续阶段。另一类是隐藏于人员培训、口头和行为示范、以及委托方和接包方之间的各类非正规信息和知识,包含更多的隐性知识,其中也包括带有特定行业特征的知识,发生在发包方的外包合约与接发包方企业价值链的衔接过程中,以及针对客户个性化需求的创新合作过程中,属于创新的协同效应。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共同构成外包过程中知识流动和集成的主要成分,彼此的相互转化和融合是知识效应发生的重要机制,为技术后进的接包方企业构成技术学习的持续动力,其中的动力机制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构成知识的“社会化”过程。外包发包方为主体的信息和知识转移推进外包的动态技术效应。以ITO活动为例,这个转化的表现如下:首先,在外包准备阶段,企业安排接包方企业的相关管理和技术人员到本企业考察和调研企业信息与数据管理的特点和问题;其次,发包方企业派相关专家和技术人对接包方企业实行包括服务标准在内的专业培训;最后,在服务项目递交和调整过程中与接包方技术和管理人员就服务的质量和各类细节频繁进行的沟通。其中涉及到信息包括服务质量要求、外包管理模式和相关的技术诀窍。这个以人员接触和交流为主的互动过程客观上传播了大量隐性知识,为接包方企业的相关技术和管理人员尽快吸收,并转化为自身的知识“储备”的一部分,成为接包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隐形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构建知识的“外部化“趋势,即非正规知识向正规知识的转型,以BPO为例,双方企业之间的沟通至关重要。接包方企业参与到发包方企业市场战略和相关策略的具体构思和实施过程中,激发学习效应,接包方企业通过写工作报告、完善客户的操作规程等手段使得一些非正规知识成为可以符号识别的正规知识,充实接包方企业的知识库,构成了相对“正规”的信息。
此外,企业在此基础上根据商业动态结果不断改善服务供应,不仅使得隐性知识得以不断积累,也帮助接包方企业超越发包方企业的要求探索服务功能和模式上的创新,在BPO活动中,由于外包供应商作为接包方能得到的佣金是基于“不见效不给付”的模式,这一风险的存在使接包方企业自身具有强烈的提高技术投入的动力,以此实现高质量、高效率完成目标产品(服务)的目标。而接包方企业在与大客户(尤其是大跨国公司)的长期合作中,发包方企业自觉地广泛收集相关信息并谋求创新的自我激励,通过对方的反馈在提升服务供应能力过程中“去芜存菁”,构成强化发包方技术外溢效应的一个条件。在总体ITO外包[2]活动中,企业将整个信息管理的硬件系统连同软件附加支持系统都交给服务供应商,后者对前者的整体经营和市场行为将有全面的了解,也是加速知识外溢的有利因素。
2. 接包方的技术升级——价值链的视角
全球跨国公司主导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格局以及服务业自身的知识密集化是目前国际服务外包的两股驱动力,前者表现为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在以国际外包为载体的垂直非一体化模式,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 Based Service)国际化进程中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两者是我们解读服务外包对接包方技术升级影响的出发点。对于接包方而言,通过外包活动嵌入到相关服务产业的国际价值链中,而其动态效应则体现为自身技术能力获得来自外部关联载体的支持和激励,具体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服务业价值链内部的“模块化”治理结构对接包方带来双重影响。随着新一代通讯、信息和网络科技彼此之间的高度融合,企业应用技术的可分性大大提高,对产业组织形态带来的影响体现为非股权模式的产业国际化路径日趋活跃,价值链的“模块化”趋势得以强化,带来两个方面效应:一方面,外包双方主体之间的生产(服务)分离形态使价值链“片断化”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对产业组织模式带来冲击,对接包方而言,承担服务价值链中不同片段与不同功能企业的知识需求往往局限于价值链的某一功能或者某一工艺流程(管理流程)的要求上,因此企业的技术获取(从发包方企业那里)和扩散相应地囿于价值链内局部性的技术特征,而不具备整体性。这个态势对企业的专有技术能力术水平的直接效应主要是提高了局部性而非整体的专业化技术水平,对登上技术阶梯的高级阶段相对不利。另一方面,服务产业特有的即时应对客户需求的目标客观上要求每个高度专业化的价值链模块结点之间保持紧密的合作,多边的用户需求对应的信息和知识的不确定性要求拉近了服务提供方(承接外包的企业)、外包需求方(客户)与服务系统集成方三方主体。在ITO和BTO情况下,尤其需要合作双方围绕动态的商业动向、管理人员的服务流程进行高效迅捷的反馈,不仅可以应对多变的需求,而且就长期效益而言,除了预期成本管理目标的实现,还体现为对接包方进一步创新的激励,基于专用性资产的技术优势和及时的信息沟通实现“超额”的积极影响,成为外包标的“附加价值”。
其次,基于外包模式内在的动态发展承包方企业获得技术升级的空间。服务外包市场上的大客户,往往是行业内领先企业,借助外包推进“归核化”战略,集中资源投入到价值链内以研发为主的高端环节,有助于扩大创新成果。在目前全球知识和创新国际化在技术上日益便利的条件下,这个过程催生了服务外包沿着知识要素的分享和协作谋求创新。目前,BPO外包在一些跨国的服务供应商的推动下谋求升级,向BTO(Business Transformation Outsourcing)模式转型,即包含更多的服务手段的创新和管理技术的创新,实现客户业务流程的转型重组和创新带动作用。以IBM公司为例,目前在财富会计、采购、人力资源、客户关系管理和保险后台作用等领域广泛推进BTO业务,以最佳实践作为基准,将流程、人员和技术的转变与外包业务模型结合在一起,帮助客户的整体业务灵活应市场竞争。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外包需求企业和外包服务专业供应商谋求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合作,后者基于自身的专用性资产与前者的企业资源整合战略相契合。服务外包目前另一个发展动向是KPO(Knowledge Processing Outsourcing),这个新业务类型是在BPO基础上的服务和外包模式的双重创新,主要是通过广泛利用全球数据库以及监管机构的信息资源,经过即时、综合的分析研究,将报告呈现给客户,作为决策的借鉴。KPO的流程可以简单归纳为:获取数据——进行研究、加工——销售给咨询公司、研究公司或终端客户。这个外包类型对接包方自身的知识积累和创新基础设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是服务外包以发包方的创新需求和接包方自身的技术能力为附加值度量的价值链上移。三者之间对应的价值链区段呈现由低到高的特点(见图1)。
IT 外包 ITES 外包 知识处理与流程创新 业务流程管理 IT基础设施铺设与服务 IT和ITES外包服务序列 价值链维度 BPO ITO 研发与设计 制造环节![]()
![]()
图 1 服务外包沿价值链维度的动态升级序列
资料来源:于慈江,《接包方视角下的IT和ITES离岸外包——跨国服务商与东道国因素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
注:由于BTO和 KPO都大量借助IT基础设施(电信和数据网络),并依赖大量IT专业人才,因此两者均属于IT技术支撑的高端服务外包,又被成为ITES(IT-enabled Service)
上述趋势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机遇在于:新兴市场国家在信息基础设施上享有后发优势,同时在局部技术领域(如嵌入式软件开发)上具备综合竞争力,发展外包联盟[3]是这些企业与发达国家大跨国公司实现长期合作的契机,构建起发包方与接包方之间主动合作和协同创新的空间,也是双方开展开放式创新的现实路径。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服务供应商而言,由于其自身服务业处于扩张和转型过程中,承接国际外包的过程是他们借助国际市场和商业关联整合研发资源实现产业升级的有利条件,有助于他们从单纯的质量保证导向型的技术能力建设转向研发导向的创新能力建设。
三、外包技术效应的转化条件——基于中国现状的考虑
由于中国服务业总体上还处于技术后进状态,服务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仍相对落后,承接外包除了利润考虑之外,更需要注重其技能获取的长期效应,从外包为载体的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学习是中国企业获得技术外溢效应的首要条件。顺应当代全球服务业的发展趋势,服务外包作为产业开放型动力机制的一个层面将有助于中国服务业的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培育。
1. 外包的技术效应与本地技术研发
中国外包接包企业的技术学习和转化的效率离不开接包方企业的吸收能力的培育。与此相关的理论依据包括:国际外包活动中的技术后进企业的本地知识与国外知识网络在特定条件下产生互补效应(Paola Criscuolo, Rajneesh Narula, 2002);外包的技术扩散效应一方面受到产品自身技术属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需要本地企业的自主技术投入作为跨越“技术门槛”的条件。本地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给予的补充性技术投入对延续技术扩散的长期效应有正向作用(刘庆林,廉凯,2007);服务供应者不是作为单纯的技术接受者,而是需要在自身推进技术投入(技术努力)的条件下,以此补充从买方那里获得的技术的条件下只有当服务供应商的技术投入的激励措施被纳入到技术转移的配套技术战略中,外包过程中的技术扩散、服务供应商的技术努力和技术转移之间才能实现积极的反馈效应(Pack & Saggi, 2001)。在技术投入的措施中,对企业员工的补充性培训是一个重要手段,在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中这方面的投入对溢出效应有正的贡献(Ngo Van Long,2005)。其次,国际外包决策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需要接包方对于外包合约谈判的间接干预。相比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技术效应,外包作为非股权模式的国际化行为,在战略决策和合作方式上高度受制于相关产业上下游产品(服务)彼此的市场结构特点的影响。由于发展中国家作为上游服务供应商,与掌握行业核心价值环节的下游发包方企业之间的市场地位往往是不平衡的,导致双方在外包合约谈判中的不平衡状况。在短期内无法根本解决市场力量不均衡的情况下,需要接包方国家有关部门通过贸易代理和其他杠杆措施对外包合约涉及的市场力量进行积极的干预,构建有利于接包方利益的特定的谈判平台。
2.承接国际外包与现阶段中国服务业的升级
在国际服务外包的大部分领域,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在基于硬件技术的基础设施上已经与发达国家保持同步。目前,印度在国际ITO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已经领先于中国,并且与美国客户之间形成相对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在一些细分市场上的外包活动模式还主要是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子公司向总部或者其他子公司接外包项目,或者是跨国公司在华的直属或自控软件开发中心承担的外包项目,有别于从海外直接将业务外包给中国当地企业,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类外包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外包,而是离岸内包的一类特殊类型。
需要指出的是,在ITO和BPO国际市场上,大订单的需求高度集中于处于行业领袖地位的跨国企业,由于合同需要启动资金和运行风险相对较高,服务供应商(接包方)也集中于少数几家具有技术优势的跨国外包供给企业,由此构成的服务外包国际的生产体系具备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的特征,对接包方也有较高的技术门槛,也引发相关服务的创新能力在相关企业间进行“内循环”,这对于其他中小企业就形成一定的“排他性”。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外包市场中尚处于“非核心”位置,在一些技术和智力资源为核心优势的大项目上的技术积累可能不足。潜在的市场空间在于那些技术生命周期更替快、价值链内部模块化合作机制鲜明的服务项目上。
鉴于我国在华跨国公司集团内部服务外包(离岸服务内包)的日趋活跃,我国开放部门正经历着从承接制造外包(离岸生产)到承接生产者服务活动或局部服务功能的转型。中国目前在一些低技术密集的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但是在BPO和 KPO等高端的服务外包市场中,本土企业在利益分配和国际竞争力方面还远未掌握主动。要形成国际服务外包对为本国服务业升级的动力机制还需要产业要素组合的调整以及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企业自身技术努力和管理效率的改善,产业创新体系为平台的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在相关扶持政策方面,需要考虑外包企业的人力资源、技术投入和配套性研发活动给予激励,实现技术学习向自身技术能力和创新要素的转化。增强对国际市场渠道的控制力,缩短与终端市场的距离,消除国际市场的“隔层效应”,来获取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Feenstra Robert C and Gordon H. Hanson,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Outsourcing to
Feenstra Robert C., 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12):31-50;
Fixler, D. J and D.Siegel,1999, “Outsourc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Service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Vol 10, 177-194;
Harmut Egger, Peter Egger,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outsourcing under industrial interdependenc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2003 July;
Howard Pack, Kamal Saggi, “Vertical Technology Transfer via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1 January;
Ngo Van Long, “Outsourcing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ume 14, Issue 3, 2005;
Paola Criscuolo, Rajneesh Narula, “ A noval approach to national technology accumula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Aggregating Cohen and Levinthal”, MERIT, Infonomics Research Memorandum Series, 2002;
程新章,《企业垂直非一体化——基于国际生产体系变革的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顾磊,刘思琦,“国际服务外包: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模型”,世界经济研究所,2007年第9期
刘庆林 廉凯,“FDI 与外包:基于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对比分析”,经济学家,2007年第2期;
卢锋《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产品内分工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卢锋,“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问题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
孟庆亮,服务外包国际化的经济学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08年第一期
刘志彪,服务业外包与中国新经济力量的战略崛起,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康灿华,阮飞,“知识溢出效应及我国软件外包企业价值链提升路径”,商场现代化,2007年第10期;
谭力文、田笔飞,“世界主要外包参与国的外包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管理现代化,2006 年第1 期。
潭力文,“外包,OEM与核心竞争力”,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于慈江,《接包方视角下的IT和ITES离岸外包——跨国服务商与东道国因素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
朱钟棣、张秋菊,“跨国外包与技术进步因果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VECM的长、短期因果关系检验”,2007年“贸易增长、贸易利益与贸易模式变革”理论研讨会论文
[1] 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是指那些已经正式成文和体系化的知识(encoded Knowledge)这类知识能够方便地被合并、提取、储存和转移,隐性知识是指那些隐含于人的身体和头脑不易编码和传播的知识,由于内化于人的头脑而更多地需要人员交流来实现转移,隐性知识可以再具体区分为实践性知识、抽象性知识和嵌入性知识(Polanyis, 1962; Collins,1993),这类知识的扩散与相关组织的组织行为方式有密切关系。
[2] 总体外包(Total Outsourcing)是相对于选择性外包(Selective Outsourcing))的一个概念,前者是指企业将有关数据和信息管理的硬件和软件服务都外包出去,后者是将一项外包业务视为一组活动,企业将其中某些活动外包出去。相关分析详见 Lacity, M and Hirschheim, R.,(1993) “ Information System Outsourcing Myths”, Metaphors and Realities, John Wiley & Sons Ltd.
[3]ITO和 BPO两种新兴的服务外包对双方的技术合作由合同纽带的短期合作转向更加长期和平等的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后者的模式因为接近企业联盟,也被称为外包联盟。它作为一种准战略联盟或类战略联盟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