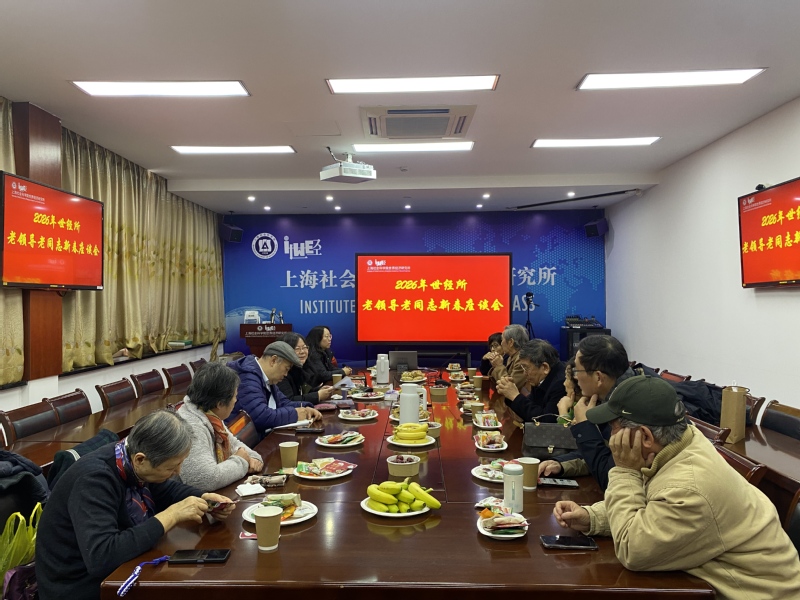根据“科学发展观”为主旨的发展战略中的基本原则,不少学者就我国利用外资问题都提出了提高“外资质量”这一主张,指出需要调整利用外资政策的导向,改数量导向为技术导向,已经有专家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包括建立要由专门的技术小组对参与外资项目审批时的技术鉴定工作等。诚然,这对于提高今后提高外资项目技术含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但是,就借助外资提高行业的技术水平这一我国外资政策的初衷而言,除了对外资项目本身的技术含量的考察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巩固并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的技术关联,推动溢出效应的形成,使之成为以合同方式为基础的技术转移的补充,以此促进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的提高。
技术溢出效应的机制与现状
基于行业内生产链纽带的关联,包括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在发展中国家,后向关联是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实现合作的主要方式,是当代跨国公司实现本土化生产,构建国际化产业网络的主要模式,在生产关联过程中发生的技术学习和技术扩散效应成为推动本土产业技术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个渠道虽然属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外部效应的体现,在当前以合约形式确定的技术转移方式效应有限的情况下,成为本土企业技术水平提高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方式。目前,蕴涵技术溢出效应的生产关联模式主要有配套生产关系、OEM合作等,直接的技术联系则包括合作研究项目,合作建立RD中心等活动。这些关联模式下两类企业的合作,尤其是人员的交流与接触成为促成技术“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才流动效应”的源泉,构成综合的技术溢出效应。其中,在现实中发展最为活跃的关联模式就是OEM 方式和零部件配套生产关系,目前在中国沿海的电子产业中这个模式成为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发展产业内关联的主要载体。作为OEM 购买方的企业除了台湾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外,越来越多的欧美国家也成为大量中等技术电子产品的OEM买家。以电脑制造产业为例,一部分本地企业提供完整的产品,例如电脑整机的生产或组装,而另一部分企业则是提供一般元器件和外围附件,两者在产品价值链中都是在制造环节,前者获得的利益相对多一些。我国沿海城市的一些小型IT企业已经成为台湾电脑厂商国际供应网络中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其中广东东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台资企业在当地已经形成了大企业为中心,大量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配套企业、关联企业和提供低技术配件的下游企业的一个完整的生产供应网络,已经形成台资企业个人电脑生产95%的配套能力。该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电脑加工制造业基地。当然,在这个地区内的本地企业与台湾的投资方之间一部分是OEM的合同联系,另一部分企业则主要提供处于价值链末端的附件和外围产品,并不完全是OEM的关联模式。在上海IT业内,当地企业大约60% 的生产活动是在OEM合同关系下进行的。
虽然OEM 的合作关系在本质上还是一种双方在产品加工范畴内的合同关系,但是在OEM合同实行过程中,供求双方都有动机,因此外商投资企业一方一般会给予一定的技术指导和扶持,帮助OEM 的本地供应商提高产品质量,成为形成技术溢出效应的一个渠道。这类技术关联活动一般表现为,对当地企业生产工艺的规范化和质量标准提出了要求,但是这样的技术关联对企业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根据一项在上海、深圳、北京和苏州进行的有关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土配套与关联企业的调查(江小涓,2002)显示,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技术支持包含的各种方式中,设定质量标准及其监督执行占了78.4%, 提供技术支持的方式占了64.7%, 持有当地企业股份, 或者共同投资实现技术开发的比例则非常小。
表 给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生产配套的本土企业接受外商技术支持的模式
技术支持的模式 | 占所有样本企业的比重 |
监督质量标准的实行 | 78.4% |
提供技术支持 | 64.7% |
持有当地公司的股份进行技术开发 | 23.6 |
与当地公司共同投资开发技术 | 11.7% |
资料来源: 江小涓,2002
溢出效应产生面临的不确定性
技术溢出效应作为以外商投资企业对本土企业以非合同方式实现的技术扩散的结果,效应发生的两端分别是作为源头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作为溢出效应接受方的本土企业,从目前中国接受外资的状况看,外商投资企业,本土企业,以及作为溢出效应实现过程的两者之间的关联活动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包含着一些不利于技术溢出效应的特征。
首先,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独资化”倾向不利于相关的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新技术的高地与活跃的技术开发活动地源头。当前,随着WTO 框架下市场准入承诺的逐步兑现以及跨国公司内向型投资力度的加大,以独资企业为模式的外商投资占整个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个倾向的发展无疑更加有利于跨国公司实现其全球战略,尤其是在技术转移与当地研究开发活动上独资企业的主动性要强得多,尤其是在国际大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的投资格局下当地的外商独资企业是这个网络格局下的一个节点,该类企业的技术投入是跨国公司母国全球技术战略安排下在特定地区的体现,因此,相关的技术转让的界限、程度和范围都是由跨国公司母国按照总体性的技术战略导向而严格规定。就现有的状况看,独资企业内的研究开发活动更加倾向于对母公司产品进行基于当地市场特征的改造,而非带有科学研究性质的开发活动。因此,以市场导向为投资动机的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本身更加强化了当地产业在产业的国际化价值链上所处的低端功能。
其次,随着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跨国公司单个企业的竞争也逐步转变为企业集团或者企业联盟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向在产业内部关联上也发生了变化,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趋势是随着大型的生产性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扩大,全球网络中的来自其它国家的配套企业也相应进行跟随式的投资,出现了产业链的连锁转移,成为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趋势的“系统化”、“配套化”的趋势,如制造业企业转移后,会带动包括物流、后勤服务相关配套产业的跟随性的产业转移、投资国的中小企业也随之推动国际化的步伐。这个趋势致使东道国产业链中出现了核心跨国公司与配套跨国公司相继投资的现象,使本地的供应链也呈现国际化的趋势。一个显著的结果是相关行业的产业内部的跨国价值链网络关系整体复制到中国。在这个网络中,技术的转移和合作,对本土企业构成了相对的排斥性,跨国公司与上海本地企业之间的联系弱化,这个状况显然不利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
第三,在技术溢出问题上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是,溢出效应不是在关联活动的基础上自然发生的,它发生的程度依赖于接受企业(本土企业)自身的技术能力,因此,影响技术能力的本土企业一系列地要素和要素组合的方式都成为影响溢出效应产生的因素,其中本土企业人力资源水平的高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产业案例看,我国电子通讯行业的一些独资、合资企业与本地配套商在对跨国公司技术的适应性开发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和西门子所开发的中文手机等高可及通讯产品,基本上也都是以中方技术人员为主,在研究和改进了原来的技术后,在我国本土开发的,在这个过程中,本地的科技人员得到了锻炼,但是他们的贡献仅仅服务于跨国公司。事实上,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中相当比例的科技人员是由本地企业“跳槽”而来的,这些研究人员很少再有返回原企业,尤其实国有企业,这导致国有企业原有的技术精英流向跨国公司,而一些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也基本上倾向于到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中心工作,这两个方面导致大量本地的优秀人才在高薪的吸引下流向跨国公司,这个现象可以成为“国内范围内的人才流失”。而且在国有企业人员流失的情况下,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的科研机构一些属于保密范围的技术和研究项目也随着科研人员一起流向跨国公司,这实际上导致了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向跨国公司的免费逆向技术扩散。因此,理论上构成外资积极效应的“人才流动”效应在研发中心的情况下很少实现。
上述三个方面是技术溢出效应发生过过程中外部环境隐含的一些不确定性,为了消除这些因素构成的对溢出效应的不利影响,除了本土企业自身的努力以外,政府的相关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各类政策成为构建一个有利于溢出效应的制度环境的条件。以韩国为例,在70、80年代,韩国政府推出与培育技术学习能力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对企业R&D活动的优惠融资政策;对私有部门技术发展的协助;对原创性技术和产品开发活动的给予地优惠融资;通过大学相关专业的发展和企业内部人员培训培育人力资源以及扶持技术研究的基础设施。这些相关的措施是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开始推行的,除此以外,另一个重要的政策导向是对于民营企业这类相对学习能力较强的本土企业在融资和其他经营活动上平等的待遇,甚至更加积极的鼓励措施,扶持他们技术能力的成长,改善本土产业总体的学习和吸收水平,促进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