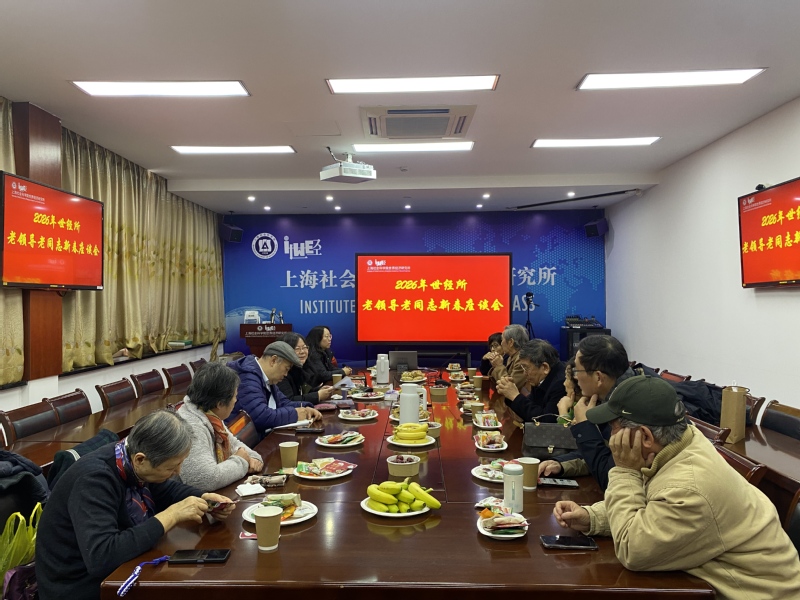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胡晓鹏研究员,2011年11月26日在《文汇报》发表演讲稿“用机制设计培养责任意识”。
文章全文如下:
经济学的责任内涵就是为他人利益考虑并付诸行动
从经济学角度看,何为责任?经济学研究市场,关注资源如何配置,而市场是经济主体实现利益的一种手段。所以,利益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关健词。在经济学看来,责任的内涵就是为他人利益考虑并付诸行动。
经济学上的责任有四个特点。第一,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中每个人的利益都天然地与他人利益绑定在一起,即市场经济是一个互惠共赢的体制。第二,任何违反他人利益的行为,都将遭到市场的惩罚,如违背诚信,所有经济主体都有动力不再和这个人合作,他也就无法获得此后的可持续利益。第三,在纯理论框架下,责任具有自实现机制。其前提包括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和独立,以及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平等的经济关系。所以,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应该是自由和平等的,而责任则体现为博爱。
但从理论的世界回归到现实,上述推论很难成立。由此得出第四个特点,在追逐利益的现实世界里,市场经济本原意义上的道德契约被法律规定下的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法制契约所取代,因此,市场经济是被法制的。
“守法缺德”的三种表现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责任缺失
依据法律和道德两个维度,可以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四个类型。其中,守法有德是全社会所倡导的行为规则,而违法缺德和违法有德都涉及了违法问题,这需要以法律制度来监督和约束。因此,探讨责任缺失的重点就是守法缺德,即经济主体在不完善的市场体制下,合理地不为别人利益着想,甚至践踏他人利益。这有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以不作为方式直接践踏他人利益。即不采取任何行为,或者该为的不为。情形之一是道德风险,比如不打借条时的借钱不还,其实质是权利享受在先,而责任付出在后。情形之二为机会主义,小悦悦事件中包含了路人出手相救可能带来的某种损失,这种可能性在南京彭宇案或天津许云鹤案的负面影响下,被进一步放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做了好事受惩罚,谁还会做好事呢?
第二,以转嫁方式直接践踏他人利益。即有实际行为但建立在损害别人利益之上。情形之一是剥削,剥削的存在源于不平等。黑心包工头之所以可以“黑心”,源于他与农民工之间不对等的关系,因为资本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情形之二是外部性,浙江某能源企业乱排污就是典型案例。这里,履行小责任是建立在损害大责任的前提下,其实质是个人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而转嫁社会成本。
第三,以道德作假方式间接践踏他人利益。最近网络上爆料,孕妇摔倒众人帮扶的案例是炒作,这种事情足以令社会痛心。社会追求真善美,市场经济追求诚信,这种道德作假带来的最大危害在于,通过破坏社会诚信机制使人们把遵守道德规范和担当责任视为负担,甚至助长冷漠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理动机。所以,道德作假虽然没直接损害到任何人的利益,但损害的是每个人的长远利益。
税收、补贴、产权改革等机制设计可帮助治理责任缺失
如何治理责任缺失呢?经济学的关键词就是机制设计。机制设计的重心在于改变行为主体的激励结构——一句话,你不愿做的事情,我赋予你一种奖励让你做;你不该做的事情,我给你一种事前惩罚不让你做。内容主要包括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即你做这件事要比不做好,以及你按照最优的方式去做得更好。我想这是经济学作出的睿智的答案。如税收、补贴、产权改革、立法和社会规范。
对应于刚才的三种“守法缺德”形式,可以有这样的机制设计。
在“作假”问题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作假的短期成本,即一旦发现便给予高额惩罚,这多以立法的方式完成;但从长远看,只要作假的预期收益高于其预期成本时,作假就不可能被杜绝。因此,这需要建立起一种“捧真抑假”的市场风尚,也就是在交易规则上建立起不和作假企业发生交易的惩罚机制,使那些不诚实守信者无法在阳光下生存。
对“转嫁”问题,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一是不对等情况的转嫁,由于不对等的关系成为经济主体赚取超额利益的手段,因此,简单的物质惩罚很能奏效,最普遍的做法就是立法强制恢复对等地位,如《劳动法》、《反垄断法》;二是针对无视大责任的转嫁,这在实践上多运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对污染征税,改变污染者扩大污染的动力;二是污染权买卖,即污染企业拥有一定额度的污染权,节约下的指标可通过交易获得收益,这也会降低污染者扩大污染的动力。
在“不作为”问题上,解决借钱不还最简洁的方法则是打借条,因为有了借条就能得到侵权法的保护,这将会增加借钱不还者的预期成本;同理,即便是不打借条,如果有抵押物的存在,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在“见死不救”案例中,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分析,一是增加见义勇为者的期望收益,即设立见义勇为救助基金;二是通过立法增加见死不救者的成本,即将见死不救的行为定为违法行为;应当说,这两种方法都是通过外在物质刺激方式来改变人的行为模式的,很难说能真正营造起符合社会道德伦理的人性良知。由此,我们试想如果摔倒在路边的老人是我们自己的父母,那么,做儿女的看到了会无动于衷吗?
道德建设是否可以弥补过度功利化的机制设计
由此我想提出两个思考。机制设计并不是那么完美,当我们把人的道德追求基于一种完全功利化的机制设计中,究竟是把人的道德引向更高的起点,还是拉下了水呢?在某些小学设置“道德银行”后,一个孩子拿了10块
最后我想引用一句我很受感动的名言:当远古时代的神,在丧失其权力的同时又都从坟墓中走了出来,以求支配人类生活,开始永恒的爱。对现代人来说,对现代青年来说,最困难的是安于现状。寻求那种体验的努力是从这种意义上的渺小做起的,因为渺小是无法辨别的时代的宿命,也是责任担当的起点。
本文源自《文汇报》2011年11月26日第8版“从不同学科背景、以不同视角关怀现实,上海社科新人接力演讲:直面责任焦虑走向责任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