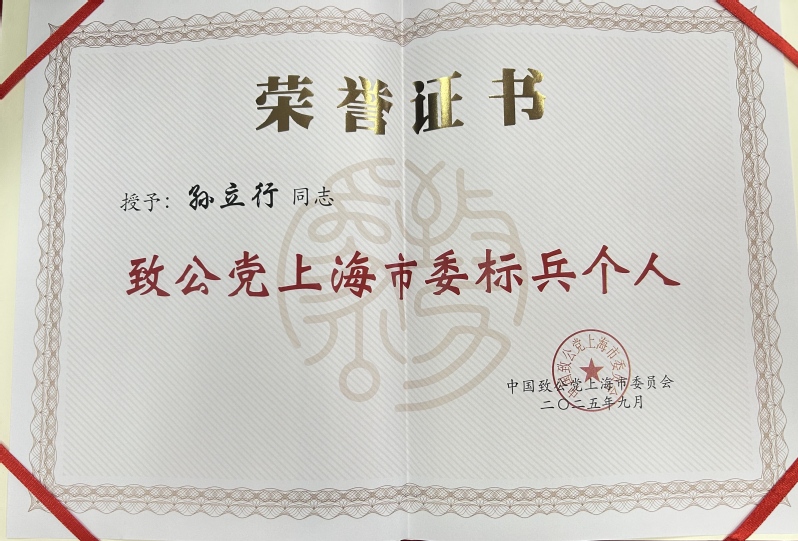●在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出现内生性抑制现象,即因企业过多依赖自我统供服务业务,致使服务业的规模、结构难以达到一个较优的水平。其作用包括内生性服务因没有完全独立致使服务业总量和结构无法提升,也包括因其没有独立成为产业所引起的对外生性服务业的联动作用的受限。这一点恰恰反映了上海的实际情况
●当我们积极从外部力量着手促进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服务业的结构问题,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内生性转化的问题。如果能够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某些现代服务行业,不仅有助于服务业规模的提升,也会因服务行业之间的联动性而盘活整个服务产业,同时,也将确保上海先进制造业竞争实力的继续提升
●加速内生性服务产业从大型制造企业集团分离的进程,是上海提升有效协调制造产业与服务产业的重要关节点,也是切实落实“四个率先”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率先不仅仅代表着时间,它更是一种推动上海全面发展、快速发展的压力。在这一压力的驱使下,必须大胆尝试运用新的手段、新的理念来促进上海经济全面、持续、快速的发展
发展“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是上海“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重要任务,而实现“四个率先”、建成“四个中心”,进而勾勒出现代化的大都市则是上海要求达成的重要目标。显然,这里面有五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如何提升现代服务业的现有规模和整体素质;二是如何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联动发展,进而切实达到三二一产业共同发展;三是在寻求上海整体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大型工业企业集团的功能该如何定位?其引领作用又该如何发挥?四是要建成“四个中心”,突破点该放在哪里?五是如何依托于大型制造项目和重大产业基地切实提高上海的城市创新能力。
应当说,全面解决上述五个问题并非易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困扰上海经济发展的难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金融业的发展以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二是服务业的“短腿”问题。虽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果敢的试验,但实际成效总是不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其实,当我们积极从外部力量着手促进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服务业的结构问题,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内生性转化的问题。比如,我们所熟悉的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行业,其原本就是独立于工业制造业的,但还有很大的一块服务领域,如设备租赁、销售服务、技术研发等却与制造企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是由于这种结合的性质,使得这些服务业务往往只与特定的制造企业集团关联,不仅造成它们的发展空间极为有限,也使得整个上海的现代服务业因缺乏这些原本可以独立运行的服务产业的支撑而活力不足。
上海是一个制造业实力非常雄厚的地区,且国资、大型国有企业的比重也都比较高。在通常情况下,这类地区的政府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也都比较强。与工业不同,第三产业或者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不主要取决于资源的集聚和整合能力,而是依赖于服务的效率、服务的质量以及市场规模的大小。显然,以政府的强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直接驱动服务业的发展,其效果就不见得非常有效。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能够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某些现代服务行业,不仅有助于服务业规模的提升,也会因服务行业之间的联动性而盘活整个服务产业,同时,也将确保上海先进制造业竞争实力的继续提升。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来支撑上述推论。
其一,在通常情况下,一些服务性的业务往往在企业集团内部解决,我们可以把这种服务业看成“内生性服务业”;与此不同,一些服务业,如银行、信托、保险等,它们原本就是由独立的服务性企业经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外生性服务业”。这两类服务业在经济活动的属性上并无不同,但最大的区别有两点:一是统计数字上只显示外生性服务业的情况;二是内生性服务业与外生性服务业之间互动的界面不是市场平台。
其二,在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出现内生性抑制现象,即因企业过多依赖自我统供服务业务,致使服务业的规模、结构难以达到一个较优的水平。其作用包括内生性服务因没有完全独立致使服务业总量和结构无法提升,也包括因其没有独立成为产业所引起的对外生性服务业的联动作用的受限。这一点恰恰反映了上海的实际情况,在长期关注于外生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时候,我们忽视了服务业内在的联动规律。
其三,内生性服务业的外生化与以下因素相关:体制因素,市场的完善程度,专业人才的数量和素质,企业权威控制的意图。这里的体制因素可以理解为企业实际发展的过程究竟是利润导向型的,还是规模导向型的。至于其他三个因素,在字面就很容易理解。从上海的实际情况看,大型企业集团的规模导向型和权威控制意图是比较明显的,集团层面总是希望自己开展的业务无所不包,且能够完全掌控其发展趋势。表面上看,这或许会增进企业的业绩,但从全局来看,却不利于现代制造业的服务化发展趋势。
其四,依附于先进制造业的现代服务活动的外部化,可以实现服务业务的通用化,将促使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并实现产业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其机理在于扩张了产业网络的规模,实现产业能力的无限拓展,企业具有了使用资源上的无边界性。其实,从道理上讲,内生性服务业务的外生化可以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制造业集团内服务活动的外生化,其结果是促使新型服务业的产生,改善了现有上海服务业的总量,同时,因外生化带来的资源集聚可以促使服务产品的垂直差别化,进而起到优化现代服务业结构的作用;二是服务业自身的部分服务活动外生化,这主要带来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
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在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5%左右;重点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业企业集团;着力提高先进制造业竞争力,继续发挥先进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
针对这些命题,我们进一步来审视内生性服务业的外生化发展问题时,就不难发现,它对于提升上海整体服务产业的总量和素质,增强制造业的竞争力水平,甚至对于实现“四个中心”的建设目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设备租赁为例,它在性质上就是一个资本运作的活动,其间必然会有众多的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公司等的参与,同时,担保公司、法律中介等服务机构也要进入整个租赁过程。此时,通过租赁活动这个纽带将会带动大量相关服务业务的发展。显然,对上海而言,租赁业的独立、快速发展将有效缓解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裹足不前和服务业发展“短腿”两个难题。一方面,租赁业可以拉动金融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租赁活动是撬动大宗贸易活动和促进大型城市基础产业发展的催化剂,这有助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建设。当然,对于大型企业集团而言,通过剥离租赁业务,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制造设备生产活动之中,有利于制造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也是上海建设经济中心的应有之义。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大量的租赁业务被局限在企业集团内部,使得这些服务活动的服务功能、联动功能和升级功能都无法发挥出来。当然,诸如销售服务、技术研发等服务活动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上述问题。
综上所述,加速内生性服务产业从大型制造企业集团分离的进程,是上海提升有效协调制造产业与服务产业的重要关节点,也是切实落实“四个率先”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率先不仅仅代表着时间,它更是一种压力,一种推动上海全面发展、快速发展的压力。在这一压力的驱使下,必须大胆尝试运用新的手段、新的理念来促进上海经济全面、持续、快速的发展。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所副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07.07.03 版次:5
●当我们积极从外部力量着手促进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服务业的结构问题,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内生性转化的问题。如果能够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某些现代服务行业,不仅有助于服务业规模的提升,也会因服务行业之间的联动性而盘活整个服务产业,同时,也将确保上海先进制造业竞争实力的继续提升
●加速内生性服务产业从大型制造企业集团分离的进程,是上海提升有效协调制造产业与服务产业的重要关节点,也是切实落实“四个率先”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率先不仅仅代表着时间,它更是一种推动上海全面发展、快速发展的压力。在这一压力的驱使下,必须大胆尝试运用新的手段、新的理念来促进上海经济全面、持续、快速的发展
发展“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是上海“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重要任务,而实现“四个率先”、建成“四个中心”,进而勾勒出现代化的大都市则是上海要求达成的重要目标。显然,这里面有五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如何提升现代服务业的现有规模和整体素质;二是如何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联动发展,进而切实达到三二一产业共同发展;三是在寻求上海整体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大型工业企业集团的功能该如何定位?其引领作用又该如何发挥?四是要建成“四个中心”,突破点该放在哪里?五是如何依托于大型制造项目和重大产业基地切实提高上海的城市创新能力。
应当说,全面解决上述五个问题并非易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困扰上海经济发展的难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金融业的发展以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二是服务业的“短腿”问题。虽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果敢的试验,但实际成效总是不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其实,当我们积极从外部力量着手促进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服务业的结构问题,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内生性转化的问题。比如,我们所熟悉的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行业,其原本就是独立于工业制造业的,但还有很大的一块服务领域,如设备租赁、销售服务、技术研发等却与制造企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是由于这种结合的性质,使得这些服务业务往往只与特定的制造企业集团关联,不仅造成它们的发展空间极为有限,也使得整个上海的现代服务业因缺乏这些原本可以独立运行的服务产业的支撑而活力不足。
上海是一个制造业实力非常雄厚的地区,且国资、大型国有企业的比重也都比较高。在通常情况下,这类地区的政府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也都比较强。与工业不同,第三产业或者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不主要取决于资源的集聚和整合能力,而是依赖于服务的效率、服务的质量以及市场规模的大小。显然,以政府的强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直接驱动服务业的发展,其效果就不见得非常有效。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能够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某些现代服务行业,不仅有助于服务业规模的提升,也会因服务行业之间的联动性而盘活整个服务产业,同时,也将确保上海先进制造业竞争实力的继续提升。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来支撑上述推论。
其一,在通常情况下,一些服务性的业务往往在企业集团内部解决,我们可以把这种服务业看成“内生性服务业”;与此不同,一些服务业,如银行、信托、保险等,它们原本就是由独立的服务性企业经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外生性服务业”。这两类服务业在经济活动的属性上并无不同,但最大的区别有两点:一是统计数字上只显示外生性服务业的情况;二是内生性服务业与外生性服务业之间互动的界面不是市场平台。
其二,在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出现内生性抑制现象,即因企业过多依赖自我统供服务业务,致使服务业的规模、结构难以达到一个较优的水平。其作用包括内生性服务因没有完全独立致使服务业总量和结构无法提升,也包括因其没有独立成为产业所引起的对外生性服务业的联动作用的受限。这一点恰恰反映了上海的实际情况,在长期关注于外生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时候,我们忽视了服务业内在的联动规律。
其三,内生性服务业的外生化与以下因素相关:体制因素,市场的完善程度,专业人才的数量和素质,企业权威控制的意图。这里的体制因素可以理解为企业实际发展的过程究竟是利润导向型的,还是规模导向型的。至于其他三个因素,在字面就很容易理解。从上海的实际情况看,大型企业集团的规模导向型和权威控制意图是比较明显的,集团层面总是希望自己开展的业务无所不包,且能够完全掌控其发展趋势。表面上看,这或许会增进企业的业绩,但从全局来看,却不利于现代制造业的服务化发展趋势。
其四,依附于先进制造业的现代服务活动的外部化,可以实现服务业务的通用化,将促使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并实现产业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其机理在于扩张了产业网络的规模,实现产业能力的无限拓展,企业具有了使用资源上的无边界性。其实,从道理上讲,内生性服务业务的外生化可以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制造业集团内服务活动的外生化,其结果是促使新型服务业的产生,改善了现有上海服务业的总量,同时,因外生化带来的资源集聚可以促使服务产品的垂直差别化,进而起到优化现代服务业结构的作用;二是服务业自身的部分服务活动外生化,这主要带来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
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在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5%左右;重点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业企业集团;着力提高先进制造业竞争力,继续发挥先进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
针对这些命题,我们进一步来审视内生性服务业的外生化发展问题时,就不难发现,它对于提升上海整体服务产业的总量和素质,增强制造业的竞争力水平,甚至对于实现“四个中心”的建设目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设备租赁为例,它在性质上就是一个资本运作的活动,其间必然会有众多的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公司等的参与,同时,担保公司、法律中介等服务机构也要进入整个租赁过程。此时,通过租赁活动这个纽带将会带动大量相关服务业务的发展。显然,对上海而言,租赁业的独立、快速发展将有效缓解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裹足不前和服务业发展“短腿”两个难题。一方面,租赁业可以拉动金融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租赁活动是撬动大宗贸易活动和促进大型城市基础产业发展的催化剂,这有助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建设。当然,对于大型企业集团而言,通过剥离租赁业务,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制造设备生产活动之中,有利于制造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也是上海建设经济中心的应有之义。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大量的租赁业务被局限在企业集团内部,使得这些服务活动的服务功能、联动功能和升级功能都无法发挥出来。当然,诸如销售服务、技术研发等服务活动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上述问题。
综上所述,加速内生性服务产业从大型制造企业集团分离的进程,是上海提升有效协调制造产业与服务产业的重要关节点,也是切实落实“四个率先”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率先不仅仅代表着时间,它更是一种压力,一种推动上海全面发展、快速发展的压力。在这一压力的驱使下,必须大胆尝试运用新的手段、新的理念来促进上海经济全面、持续、快速的发展。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所副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07.07.03 版次: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