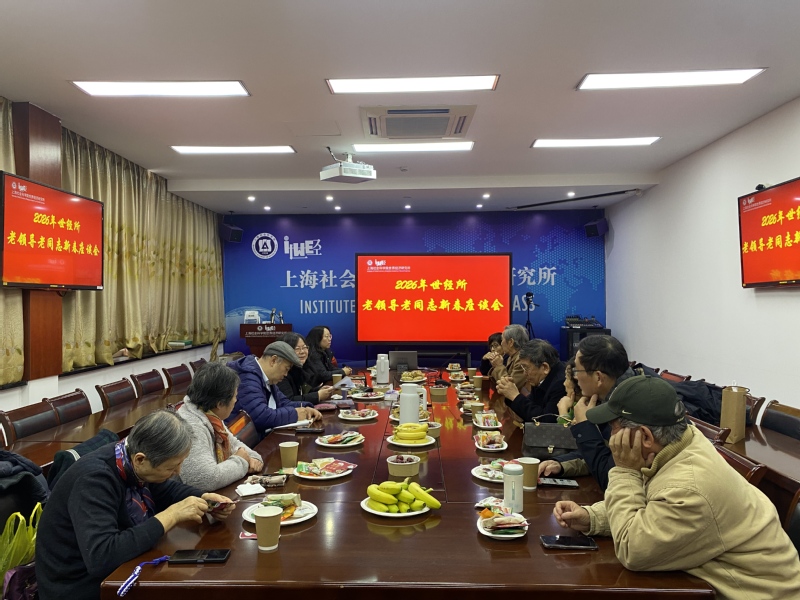打造服务型政府,发展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是上海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重大任务。它在本质上就是要禀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充分尊重经济主体的个人选择,提供满足经济主体多样化、个性化的优质产品。然而,在以国际大都市为发展目标的上海,其在相关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上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关于强制服务问题。
这个问题,在上海表现得比较普遍。比如,大多数人下班回家之后都会在自己的信箱中收到各种小报分发的广告,甚至在上海一些主要的街道上,如南京路都会碰到一些拿有广告宣传单、机票名片的孩童不断向路人发放;在襄阳路上更是有一批人不停地向路人低声询问是否需要各种款式的“皮包”。每每碰到这种情况,笔者既感慨这些广告发放者的艰辛,同时又对上海城市管理的弊端深恶痛绝。这种随意发放广告宣传单的行为有三大害处:一是行路者出于颜面勉强接收,但行不到几步就可能随意丢弃,带来的是城市环境的维护困难;二是发放传单者整体素质不高,甚至集结成群,遇到小的纠纷,很可能产生大的祸乱;三是小广告所提供的产品往往是低劣品质,但因其回报程度比较高,对正规的产品推销者和售卖者产生冲击,就是“劣币驱除良币”的道理。显然,这三大危害是上海建设和谐社会的顽疾,政府相关部门必须给予重视。
关于低质服务问题。
这里所提到的低质服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普通话问题;一是“被放纵”出来的非文明现象。大凡有乘作共交车经历的外地来沪人员都曾碰到过一个较为尴尬的事情,就是许多共交车报站员讲的是上海话,以至于每每上车后都要警惕汽车过的站数,防止出错。其实,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在一些正规化的单位和非赢利团体也经常使用上海话来交流,使得外地人总有一种难以融入的感觉。当然,用本地话来交流或提供服务并非就等于犯了怎样的错误,但上海所要建成的是国际大都市,它应当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更需要有与其相对等的实质行动。此外,还有一种是被放纵出来的非文明现象。比如,在饭店或宾馆中,随处可见抽烟者,许多外国或港澳台的朋友也都比较惊奇。其实产生这种现象,并非这些场所就没有提示,只不过根本无人来监督或提醒,以至于人人便无所顾忌。有时候在想,大多数中国人一旦走出国门也能够恪守国外的行为规范,体现出的文明素质绝不亚于老外;但为什么回到国内,似乎就“原形毕露”呢?看来,“被放纵”也是一种错误。
关于诱导服务问题。
诱导服务也许是一种商业促销手段,但它对上海城市形象的提升却并不都具有积极作用。比如,“炒股”的朋友经常会碰到证券公司打来一些所谓“免费”提供信息的服务,或者极力劝说你来上课,这其实就是一种诱导。更有甚者,孩子刚刚出生,一些专门提供婴儿用品的商家就给你打来电话,并对你的情况了如指掌。还有,一些超市为了降低成本,将一些打零工的雇员转变成“上门推销”,打着赠送“免费商品”的旗号,实质是一分钱都不会少要。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也许,这些现象对于那些欠发达的城市或地区而言,尚可容忍;但对于上海这样一个自称为经济发达的城市,就显得非常不合理了。一则,这种现象往往助长不良风气,比如,医院从利润的角度考虑,会把病人的资料转卖给某些商家;二则,这种以“免费”为基础的诱导服务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质,使得社会的和谐程度大打折扣。
鉴于上述三种现象的种种弊端,笔者认为:规范上海不良服务的工作已刻不容缓,这不仅仅是关系上海城市形象的问题,也是上海在迈向新的发展阶段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总体思路上,要坚持以惩戒和引导为手段,以制度约束为根本,以规范发展为目标的认识逻辑。
具体来讲,对于那些以赢利为目标的强制服务或诱导服务,决不能姑息,发现一例就要清查一例。为此,要切实建立举报问则制,可以以网络的形式进行投诉,政府要专门成立工作小组进行核实。当然,对于清查结果要及时通报,形成“群众举报——政府清查——群众监督”的良性运转机制。同时,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可以专门开辟一块场所,由那些提供专门服务的人员在这里集中,需要这种服务的个体可以自由选择。因此,“惩戒+引导”是两个必不可少的、同时进行的工作环节。此外,对于那些服务质量不高或者服务不到位的低质服务者,要加强约束。一方面,必须有健全的上岗认证制,确保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养达到一定水平,另一方面,要附之于信息通报制。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政府部门是不能以行为主体的身份介入到企业的运营之中(涉嫌违法除外),但政府可以通过褒扬先进、鞭策落后的手段提升相关单位的服务质量。比如,政府相关部门接到投诉,一经核实,就要对服务人员所在单位记录在案,并在其所拥有的评级账户上扣除分数,到一定时间以后,政府要定期发布服务质量欠佳单位的名单,使广大民众具有知晓权,并发动民众实施集体监督。其实,上述措施只是一种尝试,也许运营和维护成本会比较高,但对于上海形象的维护和城市品牌的提升却具有重大意义。说到底,如何建立一套运作规范、执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才是确保服务质量不至缩水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