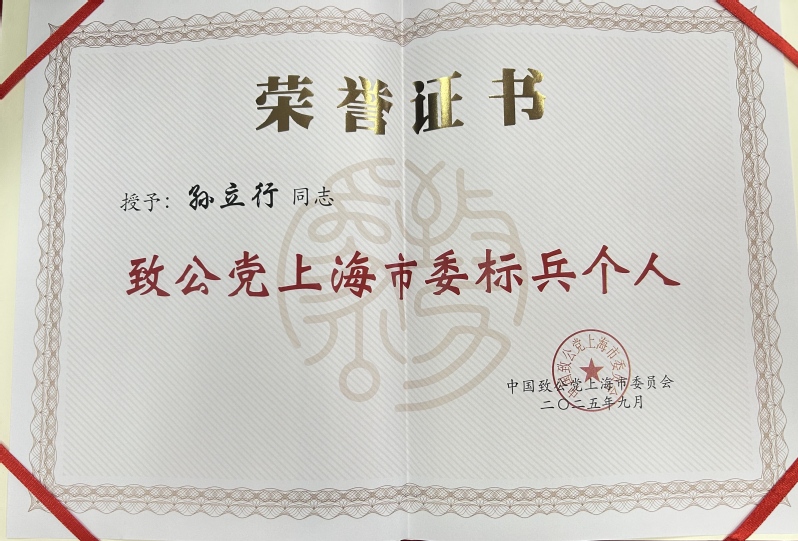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具有世界意义。理解经济全球化及其运行机制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的关键,也是分析中国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地位与作用的关键。
一、 要素集聚:全球化经济的基础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现象。众多国际组织和专家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把全球化定义为“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度融合。”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2000)对全球化的定义是“商品、服务、资本、信息、思想和自然人的全球流动”。Prakash和Hart(1999)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扩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
商品的国际流动早就存在,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两者并非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或核心特征。真正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是要素的国际流动。正是要素的国际流动才把各国独立的生产过程变为真正的世界性生产过程,并促进了跨国公司这一全球化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因此,要素的国际流动才是经济全球化区别于世界经济以前发展阶段的本质。一些学者也强调了这一点。如罗肇鸿(1998)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的一种运动状态,主要是讲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余永定(2002)也明确指出,“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在世界处于一种理想状态的情况下,全球化作为这一流动过程的终点,意味着资源的最优配置已经达到了它的空间极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帕累托优化。”
要素国际流动的目标是寻求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但是,要素的国际流动并非意味着要素会对称地或均衡地在世界各国之间进行,恰恰相反,要素国际流动导致的是要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集聚。也就是说,一些国家的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跨国经营网络等广义要素[1]会集聚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使这些国家或地区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要生产者。要素集聚是全球化经济一种特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它构成了全球化经济的基础特征,也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实现优化配置的具体体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素的国际流动存在着结构性的偏向,主要表现为资本、技术、优秀人才等高级要素极易流动,而一般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低级要素的流动不充分甚至基本不能流动,由此导致要素流动主要表现为高级要素拥有国家的要素向某些低级要素拥有国家流动。[2]要素流动的结构性偏向导致了要素集聚的结构性偏向,主要表现为高级要素拥有国家的高级要素以资本形成等方式向某些低级要素拥有国家集聚,从而生产加工能力和出口能力向这些低级要素拥有国家集中。这一流动的核心特征是:流动性较强的要素向拥有流动性较低要素的国家流动,这些国家由于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趋势而成为要素集聚地。因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和跨国经营网络等广义要素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量集聚,世界主要的跨国公司纷纷把生产基地、地区总部甚至研发中心向该地区转移。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了世界要素的主要集聚地,由此也成为了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3]
作为全球化经济的基础特征,要素集聚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推动了要素合作这一新型的国际分工形式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大发展之前,国际分工体系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工业革命至二次大战前的中心外围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垂直分工阶段和20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分工阶段。尽管存在着分工形式和层次上的巨大差异,但这三个阶段都是典型的以产业或产品的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国际分工。各国主要使用本国的生产要素生产和出口,物质产品的流动而不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构成了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获得了迅猛地发展,要素的国际自由流动促进了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的形成——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在某些国家集聚,形成某一种或几种产业,并面向世界生产和出口。此时,传统的贸易结构已不再是国际分工的主要标志,生产要素的国际差异才是国际分工的基础和核心。正如有些专家所指出全球化经济中的国际分工是“要素分工”,这是完全正确的。[4]进一步而言,要素集聚已经使得 “分工”(division of labor)或“国际分工”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更多地深化为一种“合作”或“参与”,即各国以一种或几种特定要素参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化生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国际专业化,应该称为“要素合作”型的国际专业化。[5]国际分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全球化条件下的要素集聚导致了生产从而出口在一部分国家集中这一新格局的产生,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分工的性质,从而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
二、中国要素集聚能力的形成及世界的贡献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成为世界要素集聚最多的国家之一。随着大量资本、技术、品牌、优秀人才等高级要素的集聚。1979—2005年中国FDI实际流入额累计达到了6224.3亿美元。[6] 2003年达到535.1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297.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总体上看,中国FDI流入额约占全球FDI流入额的10%、发展中国家的25%和东亚、南亚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50%左右,2004年这三个比重分别为9.35%、26%和44.03%。[7]FDI大量集聚中国的趋势非常明显。要素的国际流动并不仅限于资本国际流动,FDI往往也具有多维属性。[8]FDI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包”,包含着资本、技术、管理、信息、知识、品牌、海外销售网络等多种要素。在全球化经济中,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是国际投资的主体,也是技术、标准、品牌、跨国生产经营网络等高级要素的主要拥有者。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80%以上的新技术和新工艺,是世界技术发明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是全球研发的主要承担者(杨丹辉,2004)。Caves(1982)也指出:在那些R&D最为突出的行业中,R&D与对外直接投资都集中于大公司手中,R&D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外直接投资也反过来促进R&D。伴随着国际资本的集聚,其他要素也随之集聚,这可以从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中反映出来。截止到2005年12月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达552942个,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50家左右已来华投资。[9]
全球要素在中国的集聚使中国逐步成为了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众多产品的产量及出口额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相关研究报告显示,2001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100多种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第一”。这100多种产品囊括了家电制造业、通讯设备、纺织、医药、机械装备、化工等十多个行业。伴随着要素集聚和生产集聚,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众多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大幅提高。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1545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5年更是达到了14221亿美元,是1978年(206.4亿美元)的68.9倍。[10] 2004年中国IT相关产品的出口额达到1887亿美元,超过美国(1631亿美元)成为了全球最大的IT相关产品出口国。[11]
众多学者在FDI意义上研究了中国要素集聚的影响因素。Cheng和Kwan(2000)以中国为例探讨了影响FDI空间布局的系列因素,发现市场大小、基础设施好坏、教育水平高低等对FDI有正面影响,而且外商投资存在“区域性自我加速”机制。Deichmann等(2003)研究认为,人力和社会资本、改革和稳定、资源稀缺性及先天条件和金融市场状况是FDI的主要影响因素。Agodo(1978)发现FDI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所创造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紧密相关。沈坤荣和田源(2002)的研究证实了市场容量、人力资本存量在决定中国区域FDI规模上的重要性。梁琦(2003)研究了FDI与产业集聚的相关性,发现地区的开放度和产业集聚所产生的关联效应是FDI区位集聚最主要的驱动力。贺灿飞等(1999)研究发现,就全国层面来讲,FDI有自我加强的效应。鲁明泓(1999)研究了制度因素的影响,发现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和对外资持欢迎的态度在所有影响FDI流入的因素中最重要。
我们认为,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要素之所以大量集聚中国,源于中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要素集聚能力。要素集聚能力是一国创造和拥有的、以吸收外资为载体的、集聚资本、技术、管理、信息、品牌、专利等全球广义生产要素的能力。中国的要素集聚能力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正是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消除了要素向境内流入的政策障碍,国内体制的不断改革创造了要素集聚的市场和体制条件,构成了集聚各国广义生产要素的强大的引力场。
改革开放对中国要素集聚能力形成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打破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中国巨大的经济活力,使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具备了最为重要的国内经济体制基础。改革激发了劳动者强烈的致富欲望,并把这一致富欲望转变为改革的巨大动力,推动着国家体制向开放型市场体制转型。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先富的示范效应成为推动改革深入进行的巨大动力。
其次,农村改革释放了近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参与国际要素合作的优势要素的形成。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数量不断提高,流动半径加速扩大,2003年外出1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总和达到了9831万人(蔡昉,2005)。另据统计,综合各方面因素,目前中国农民工保守推算超过了1.8亿,甚至有专家估计在2亿左右(刘维佳,2006)。大批的廉价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和沿海地区,极大地压低了劳动力的成本。
第三,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土地资源配置得到了优化。土地在中国长期不作为生产要素而无偿使用或低效使用,土地批租制度的改革使土地开始作为生产要素投资,农业土地的工业化使用大大提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改革不断释放出来的土地要素与劳动力要素一起成为吸引国外要素集聚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第四,分权式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使各级地方政府有了发展地方经济的巨大积极性和强大功能,从体制的内在动力上和政策的灵活性上形成了中国争取国际要素流入的巨大引力。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主要是从中央集权体制转向中央地方分权式体制。[12] 1994年分税制的改革则大大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巨大积极性。各级地方政府高度关注本地经济发展的体制。在加快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下,各级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竞相出台各种极为灵活的地方性外资政策条例,并身体力行大力招商引资,由此形成了中国争取国际要素流入的多极化的巨大引力源。
第五,稳定的、持续强化的开放政策促进的要素的流入。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地区再到实行全国开放,[13]从实行“三来一补”到大力招商引资,从“以市场换资本”到“以市场换技术”,从以引进港澳台资本为主到引进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从引进生产企业到引进研发中心,从引进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到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乃至全行业开放,多层次、多领域、多方式的开放,中国持续推进的开放极大地鼓励了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流入,促进了国际要素在中国的集聚。28年来,开放政策在保持稳定性、延续性、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时,不断加大了力度。超国民待遇的外资优惠政策,提供了流入要素在中国本地市场上的有利的竞争地位。市场的透明度和规范性不断提高,创造了跨国公司熟悉的经营环境,特别是加入WTO承诺的履行更加提高了市场准入透明规范的稳定性和法制化,有力地推动了要素的进入。此外,政府对外资的服务高度积极有效,投资软环境不断改善。综合投资发展环境不断发展。从经济发展、市场规模和潜力、劳动力价格和人力素质、政府的勤政和办事效率、政治稳定性等多方面分析,中国的综合投资发展环境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4]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也指出,中国的投资环境在过去的20年中飞速发展,总体水平领先于巴西、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沿海城市的投资环境相当优越(陈净植、刘璐璐,2003)。综合投资发展环境优越意味着中国相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强的要素集聚能力。
在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进程中,国内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形成了具有发散型的正反馈机制:改革的推进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由此导致了中国国内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国内购买力日益增强,进而引发了外部要素更多地流入,而外部要素更多地流入又促使中国经济规模更加扩大,购买力更强,从而外部要素流入更多。在这种正反馈机制作用下,由改革所推动的国内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外部要素的流入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使中国的要素集聚能力日益提升。
中国集聚现代经济中的生产要素,在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以特殊的方式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种贡献包括:第一,优化了世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效率。相对于商品的国际交换,全球化下的要素合作与分工更能够直接改进世界范围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薛敬孝、佟家栋、李琨望,2000)。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巨额资本和先进技术等高级要素在中国的大量集聚,与中国近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最佳组合。产出是多种要素组合的结果,中国大量廉价优质的要素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管理的“联姻”,从根本上有利于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世界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第二,为各国生产要素提供了大量的投资机会,使世界生产要素分享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据中国美国商会2004年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四分之三在华美国公司是盈利的,42%的公司在华的利润率超过了它们在全球的利润率(王义伟,2005)。日本对华投资企业中有82.8%的企业盈利,其中销售利润率高达9%以上的企业接近30%,部分企业在中国投资所获的利润已经成为了这些公司的支柱。[15]根据高盛公司分析,20世纪90年代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达到了8%,比美国和欧洲的投资收益率高出很多(胡祖六、约翰·安德森,2003)。第三,为世界提供了大量优质廉价的商品,提高了各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国际要素的大量集聚导致了中国商品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长。大量优质廉价的出口商品受到了全世界消费者的喜爱,抑制了世界物价水平的上涨,并大大改善了世界各国居民的福利水平。据摩根斯坦利公司的一份统计报告称,过去10年间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商品总计节省了6000亿美元。牛津经济预测机构指出,如果没有中国的商品,美国2005年的消费价格会上涨0.5%,2010年可能达到0.8%(国纪平,2006)。1998—2003年,仅童装一项,美国年轻父母就因购买中国商品节省了4亿美元。[16]第四,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巨大的出口市场,拉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在要素集聚与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进口的规模和速度也大幅提高,从而为世界各国的商品提供了日益广阔的出口市场。中国每年的进口总额从1978年的109亿美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6601亿美元,[17]进口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6%。另据世界银行(1998)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将由1992年的2.18%提高到9.19%,仅略低于美国。据统计,2000—2003年中国出口对世界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7.3%、19.8%和10.7%,进口对世界进口的贡献率分别为7.5%、20.5%和10.9%。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带给世界的绝非“零和游戏”,中国的成功能够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与稳定。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认为,将会有更多国家从中国市场开放中受益。
三、 要素集聚与中国的国家核心能力
在世界经济体系进入全球化的今天,要素集聚能力成为目前中国重要的国家核心能力。Prahalad 和Hamel(1990)首次提出了核心能力的概念,认为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拥有的能创造经济效益的、而又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独特能力。波特(2002)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分析了一个国家赢得某些产业竞争优势的原因,提出了著名的“钻石体系”理论。王绍光和胡鞍钢(1993)认为国家能力是国家(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它包括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强制能力和合法化能力。而周立(2004)将政府的动员和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定义为国家能力,认为强化国家能力就是强化国家动员和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结合企业核心能力或国家能力内涵,本文提出的“国家核心能力”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拥有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使该国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这是一种综合的、不易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独特优势,不仅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为本国创造经济收益,而且确定了该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特定地位和为世界经济贡献的特定方式。要素集聚能力的合理利用不仅能快速增加一国的物质财富,提升一国的国际地位,而且能增强该国对世界体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在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要素集聚能力的形成是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和国家能力持续提升的基础和关键,其具体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国际高级生产要素在中国得到使用,增加了中国的财富创造,扩大了中国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国际事务的参与能力以及国际谈判的实力。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进入中国,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使发达国家的要素获得高额收益的同时,也增加了中国的财富创造,使中国政府获得了大量的税收。据统计,2004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共缴纳税收5355.29亿元,占到了全国税收收入总额的20.81%。[18]由此,政府有了更高的能力提供公共产品,增加教育投入、加大农业支付转移,扩大国防支出;国家有了更多的财力进一步发展经济,加大重点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大科研的投入;中国有了更大的能力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参加国际维和活动,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巨额援助等。对流入的要素提供政府服务、市场环境服务和体制服务的收入是要素大量流入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国力增强的来源之一。
第二,要素集聚激活了国内闲置要素,提高了国内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使中国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中国集聚国际要素的特点是,以低级要素吸引国际高级要素,以闲置要素吸引流动要素。中国大量廉价供给的低级要素吸引了高级要素的参与,从而迅速提升了整体经济的结构水平。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之一就是要素投入总量的增加,中国要素投入总量增加的机制之一来自于外部要素流入的拉动。因此,由要素集聚导致的本国要素投入的迅速持续增加及其使用效率的提高是中国国力增强的来源之二。
第三,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大大增强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中国经济结构的每一个进步都意味着国际企业新机遇的创造,对外开放政策的每一步推进都意味着国际企业投资与盈利空间的扩大。中国巨大的制造能力为世界提供着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并影响着国际市场的价格,巨大的国内需求能力成为国际市场上举足轻重的购买者。尽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要素不完全是这个国家国民的,但这不影响这个经济体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因为一旦要素流入这块国土,那么其作为这个国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构成了该国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基础。正如波特(2002)指出的那样:“人力资源、知识和资本是可以在各国间流动的。高级技术人才正如科技知识一样高度流动,这种人才流动随着国际通信的发达而更显著。当一国任凭它拥有的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离去时,这一部分生产要素也就不成为该国的优势。能有效应用这些流动的生产要素、提高配置生产率的国家,通常也是国际竞争中的赢家。”
第四,整体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日益为中国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提升建立了坚实基础。巨大的经济规模从而巨大的购买力、竞争力和投资机会等使中国国家战略的每一步都具有世界意义,并从而以这种或那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与运行。中国所支配的国家经济规模日益扩大,所支配的财力日益扩大,对国际事务发挥作用的能力日益扩大,从而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要素集聚成为目前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力量提升基础和关键。要素集聚使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了要素增值这一特定的依存性,离开了中国稳定的生产投资环境,这些要素的增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难以增值。由于要素集聚的市场开放程度以及与国内巨大的购买力和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政府可以调控的对象,这就使中国的要素集聚能力可以作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力量。例如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购买力迅速上升使政府采购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
要素集聚能力是当前中国的核心能力所在,但是,要素集聚能力并非现代国家能力的全部,而只是它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经济中,除要素集聚能力外,国家可能还需要拥有两大经济能力——创新能力和购买能力。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是知识经济的日新月异,由此决定了技术创新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拥有技术创新能力也就拥有了现代经济的主导权,进而拥有全球化经济中的主导权。进一步说,尽管技术要素可以通过流动在其他国家集聚和使用,但技术所有权和技术的收益仍然归母国所有,因此自主创新能力才是更为真正的更为重要的国家能力。另外,全球化经济又是市场经济,并且是一个大部分产品过度供给的市场经济。[19]对于稀缺产品是生产者主权,而对于过剩产品则主要是消费者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主权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作用:对产品的吸收能力即一国的购买能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这种购买能力不限于消费购买,也包括投资购买。从总体上说,在现代国家的三大经济能力中,当前中国只拥有其中的一个半。目前中国在总体上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国家经济能力的最大弱点。这主要表现为中国的专利技术少,研发投入小。如在移动通信、集成电路、数字电视等核心技术领域,中国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不及国外企业的1/10;在研发投入方面,2003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265.6亿元,不及IBM的60%。[20]中美科技水平总体差距估计有15-20年,集成电路、CPU、新材料落后6-10年左右,计算机、软件和信息安全等180项技术落后5年左右。在全球R&D投入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占86%,中国仅为1.7%;全球专利方面发达国家占90%以上,国际技术贸易发达国占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8%,而中国国内授权的发明专利仅为日本和美国的1/30和韩国的1/4。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而且99%的国内企业没有申请专利。[21]中国有巨大的购买能力,进口规模不断扩大,但对这种购买能力的理解应当全面。虽然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但消费率却极低。1978年,中国的消费率为62.1%,2003年消费率下降到55.4%,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50%以下,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20个百分点。[22]而金融与企业体制的多种原因也使中国的高储蓄难以有效转变为国内投资,2005年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存差达到了92479.13亿元。[23]中国国内巨大的购买能力并不完全来自于本国居民和企业。除了迅速增长的国民收入导致的国内投资需求之外,相当一部分购买能力本身是来自于要素集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导致了进口需求的增长,经济规模在要素集聚中迅速扩大增大了本地需求和进口需求,特别是在华外国人及其商务活动的本地需求。由此说明目前中国国内市场的购买能力主要不是内生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要素集聚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集聚国际要素形成的生产规模并非一国的真实国力。实际上,只有要素所有权意义上的国家产出而非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产出才是一国国民能够支配和享用的财富,才更直接反映一国生产要素的财富创造能力,也才更真正体现一国的真实国力(张幼文,2005b)。如果不分清集聚国际要素形成的生产规模和国家真实国力的区别,就会严重高估当前中国的真实国力,从而既不利于中国国际战略的正确制定,也不利于中国真实国力的持续提升。如果在提升要素集聚能力的过程中过度依赖政策激励而不是体制优化,那么其中就可能包含着大量的不必要的利益外流,从而影响真实国力的有效提升。
四、 要素向中国集聚与世界经济失衡的性质
要素向中国集聚也导致了世界经济的新的特征,所谓“世界经济失衡”现象的性质可以从要素集聚得以解释。
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失衡成为整个世界面对的一大难题,而美国的双赤字和中国的双顺差则被看作集中的表现。就贸易差额看,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141.73亿美元,约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总额(7665.61亿美元)的15%左右,但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2005年达到2016.26亿美元,占其贸易总逆差的比例达26.3%。[24]在某些言论中,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被归咎为中国巨大的贸易出口和外资吸收能力。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中国外资大量流入和产品净流出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特点,而其基础正是全球要素的集聚。一方面,全球化要素流动使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集聚了大量的国外要素,与其低成本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出口;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构造了全球的低价供应平台,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国际投资中更多获利,从而导致这些国家更高的消费和贸易逆差。具体来说,要素集聚导致了生产型国家的形成,要素和生产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集聚,必然导致其出口能力的迅速提高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中国等亚洲国家迅速提升的出口能力发达实际上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各类高级要素在这一地区集聚的结果。同时,要素集聚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构建起了一个全球的廉价产品供应平台,它们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投资增加了其高级要素的收益,扩大了财富积累和进口能力,又因为进口产品的低价格抑制了通货膨胀,而金融资产升水使储蓄更加减少,消费更加扩大,从而更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因此,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要素集聚,是要素集聚这种全球化经济的特有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要素向中国集聚及其带来的生产与出口的集中导致许多国家的相关产业受到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全球经济的失衡。要素的流动和集聚意味着产业的转移和就业的转移,而要素流出国新产业的产生特别是工人从旧产业到新产业的转移并非一蹴而就。同时,尽管要素集聚从根本上有利于全球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在世界高级要素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结合生产出来的廉价产品出口给各国消费者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会造成冲击,也极大地抑制了原本有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相关产品的出口,从而对他国国内的某些产业和某些利益集团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引发许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持续加剧。[25]据统计,中国已连续10多年居全球贸易摩擦目标国的榜首(邵芳卿,2005)。然而当我们看到中国产品对各国的冲击只是世界要素集聚到中国进行生产并出口的结果,从而是经济全球化要求的全球产业重新布局,那么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失衡了。某些学者将失衡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中国的开放政策特别是人民币汇率政策,并因此将这种由全球化历史性变化所带来的失衡调整的责任完全归于中国一个国家,把调整的压力完全置于人民币一种货币上显然是不公正的。
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国发展模式与世界经济的摩擦与矛盾,也要看到产生这种摩擦的必然性即经济全球化下的要素集聚,尤其还要看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新发展阶段的世界意义。
对中国经济来说,大量要素集聚使中国承担了“世界工厂”的重任,使世界发展的能源和生态环境问题也集中在中国。伴随着大量的国际要素集聚中国,原本在其他国家的众多高耗能产业的生产也转移到中国。要素集聚使中国承接了相当大份额的世界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加重了中国的能源消耗。据统计,中国一次能源、石油和煤炭消费量分别从1994年的811.8、149.5和606.4百万吨标油上涨到了2004年的1386.2、308.6、956.9百万吨标油,2004年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了世界消费总量的13.6%、8.2%和34.4%。2004年中国钢铁消费量为312.3 万吨,比2003年增长了15.12%,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钢材表观消费量达到3.12万吨,相当于美国、欧盟和俄罗斯消费量的总和,占到世界总消费量的30%。[26]中国的GDP只占世界GDP的百分之四点多,但消耗的能源、铁矿石、原材料已经占到了世界总消费量的1/3左右(路风,2006)。中国在保护环境问题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伴随着要素集聚,外商投资企业将许多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中国,使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更为严重。据统计,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资产占全行业资产比重最高的10个行业中基本上都是制造业,且一半以上为制造业中的污染密集产业(谭晶荣、张德强,2005)。计量分析显示,FDI与污染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FDI对中国环境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杨海生等,2005)。尽管中国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不能完全归因于要素在中国的集聚,但要素集聚导致的大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向中国的转移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资源和环境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并因此也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中国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既有中国发展模式粗放的问题,也有世界产业转移和传统产业生产向中国集聚的原因。中国接受了这种转移,获得了发展的利益,也同样需要承担发展的责任。要素集聚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机遇期”的同时,也使中国处于“矛盾凸显期”。中国的能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的新问题,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发达国家之间也面临着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无从谈起,对世界经济而言也绝非好事。为此,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发,更从一个日益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角度出发,中国政府一方面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树立了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型社会的目标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也对外发出了共建和谐世界的呼唤,力求用新的思路、新的理念解决全球化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致力于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7]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历史性跨越。新的发展理念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未来发展道路的规划。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也包括统领对外开放的战略规划与政策导向,统领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正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发展进入一个更高阶段的表现,以科学发展观指导进行开放战略的调整是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更高阶段,致力于一个更高目标的要求。中国致力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将有利于减少国际经济摩擦,加强各国经济合作,将有利于减轻世界各国所面临的资源和能源压力,也将有利于实现更为均衡的、更高总收益的世界共赢。
(原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
参考文献:
[美]保罗·克鲁格曼(1999):《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1998):《国际经济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4—56页。
[美]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1992):《经济学》(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第45页。
[美]迈克尔·波特(2002):《国家竞争优势》(中译本),华夏出版社。
蔡昉(2005):《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得制度性障碍分析》,《经济学动态》第1期。
陈净植、刘璐璐(2003):《中国的投资环境相当不错》,《政策前瞻》第12期。
董辅礽等(1996):《集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建》,经济科学出版社。
国纪平(2006):《中国和平发展和世界共同繁荣》,《人民日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第45页。
贺灿飞、梁进社(1999):《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变化》,《地理学报》第3期。
胡祖六、约翰·安德森(2003):《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中国金融出版社,第155页。
李琮主编(2000):《世界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第432页。
梁琦(2003):《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世界经济》第9期。
刘维佳(2006):《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学习时报》第319期。
鲁明泓(1997):《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与中国投资环境评估》,《经济研究》第12期。
鲁明泓(1999):《制度因素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一项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路风(2006):《自主创新需要勇气》,《解放日报》
罗肇鸿(1998):《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太平洋学报》第4期。
邵芳卿(2005):《中国今年将第11年居全球贸易摩擦目标国榜首》,《第一财经日报》
沈坤荣、田源(2002):《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管理世界》第11期。
世界银行(1998):《中国的参与: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25、26页。
谭晶荣、张德强(2005):《对我国利用FDI项目中环境保护问题的思考》,《国际贸易问题》第5期。
汪维钢(2004):《“中国制造”的尴尬困局》,《中国企业家》第11期。
王光荣(2002):《“中国制造” 的崛起,不争的事实》,《光明日报》
王洛林主编(2000):《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王绍光、胡鞍钢(1993):《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
王义伟(2005):《28万家外企三分之二盈利》,《中国经营报》
王永林等(2003):《中国投资环境的国际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
魏后凯、贺灿飞、王新(2002):《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决策》,商务印书馆。
薛敬孝、佟家栋、李琨望(2000):《国际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94页。
杨丹辉(2004):《全球竞争:FDI与中国产业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1、209页。
杨海生等(2005):《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3期。
易纲(2002):《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国际经济评论》第5—6期。
余永定(2002):《从中国的角度看全球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编:《全球化与21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0页。
岳中刚(2005):《地区间竞争外商直接投资的福利效应分析》,《产业经济研究》第1期。
张二震(2005):《全球化、要素分工与中国的战略》,《经济界》第5期。
张幼文(2002):《全球化经济的要素分布与收入分配》,《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0期。
张幼文(2003):《当代国家优势:要素培育与全球规划》,上海远东出版社。
张幼文(
张幼文(2005b):《对外开放效益评估的主题与思路——以科学发展观对“新开放观”的探索》,《世界经济研究》第8期。
周立(2004):《中国国家能力结构变化与金融功能财政化》,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交流论文。
Agodo, O., 1978, The Determinants of US Privat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in Afric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Winter, 9(3), pp. 95—107.
Aseem Prakash and Jeffrey A. Hart, Eds. 1999,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Published by Routledge London, pp. 3.
Balasubramanyam, V. N., M. Salisu, and D. Dapsoford, 1996,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EP and IS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106, pp. 92-105.
Caves, A. E. 1982,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Economic Analysis,
Chen, C., L. Chang and Y. Zhang, 1995,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s Post-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23, pp. 691-703.
Cheng, L.K., and Kwan, Y.K., 2000, Wha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hinese Experi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1, pp. 379—400.
Deichmann, J.I., Eshghi, A., Haughton, D.M., Sayek, S., and
Helmut Wagner, ed, 2000, Globalization and Unemployment, Published by Springer Heidelberg, pp. 19.
Johnson, H. G., 1972, Survey of Issues, in Peter Drysdale, e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Asian Pacific,
Lee, C., 1997,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rahalad, C. K. & Gary Hamel, 1990,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June, pp. 79-93.
The World Bank , October 2000, Pover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www. Worldbank.org/html/extdr/pb/ globalization/ poverty globalization.pdf.
[1] 关于“广义要素”参见张幼文(2003)。
[2] 关于要素国际流动存在的结构性的不对称,参见张幼文(2002)。
[3] “要素集聚”概念及其论证首次发表于张幼文、黄仁伟等著《2006中国国际地位报告》,该书导论中第二、三节由张幼文撰写。
[4] 南京大学的张二震(2005)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的形式正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
[5] 关于“要素合作型国际分工”参见张幼文(
[6] 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统计,见www.mofcom.gov.cn。
[7] 数据根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2和2005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8] 关于FDI的多维属性可参见Johnson(1972)和Balasubramanyam,Salisu and Dapsoford(1996)的相关分析.
[9] 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统计,见www.mofcom.gov.cn。
[10] 数据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资料计算,见www.mofcom.gov.cn。
[11] 参见世界经济年鉴编委会:《世界经济年鉴》(2005/2006),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
[12] 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集权体制与分权体制的分析,可参见张宇:《集权、分权与市场化改革》,载董辅礽等(1996)。
[13] 魏后凯、贺灿飞、王新(2002)的相关研究分析表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过程与开放政策的时空过程是一致的,随着开放政策在空间上的扩展,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也相应扩展。
[14] 关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比较,可参见王永林等(2003)。
[15] 记者专访:《中国经济发展是机遇而非威胁》,转引自新华网
[16] 参见法国《快报》周刊,《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之最》,转引自《参考消息》
[17] 中国商务部统计资料,见http//www.mofcom.gov.cn.
[18] 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统计资料,见www.mofcom.gov.cn。
[19] 关于世界经济面临的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问题,可参见[美]保罗·克鲁格曼(1999)和易纲(2002):的分析。
[20] 参见吕福明:《联想买到什么,"鼠标现象"揭示自主创新诱惑力》,转引见新华网
[21] 数据来源于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
[22] 数据来源:新华网http://biz.163.com,
[23]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参见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tongjishuju/index2.asp。
[24] 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统计,见business.sohu.com/20060414/n242811750.shtml。
[25] 关于政府政策会更多的反映贸易中受损利益集团的要求的原由,参见[美]保罗·克鲁格曼和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1998)。
[26] 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年鉴编委会:《世界经济年鉴》(2005/2006),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315页。
[27] 参见胡锦涛:《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民日报》